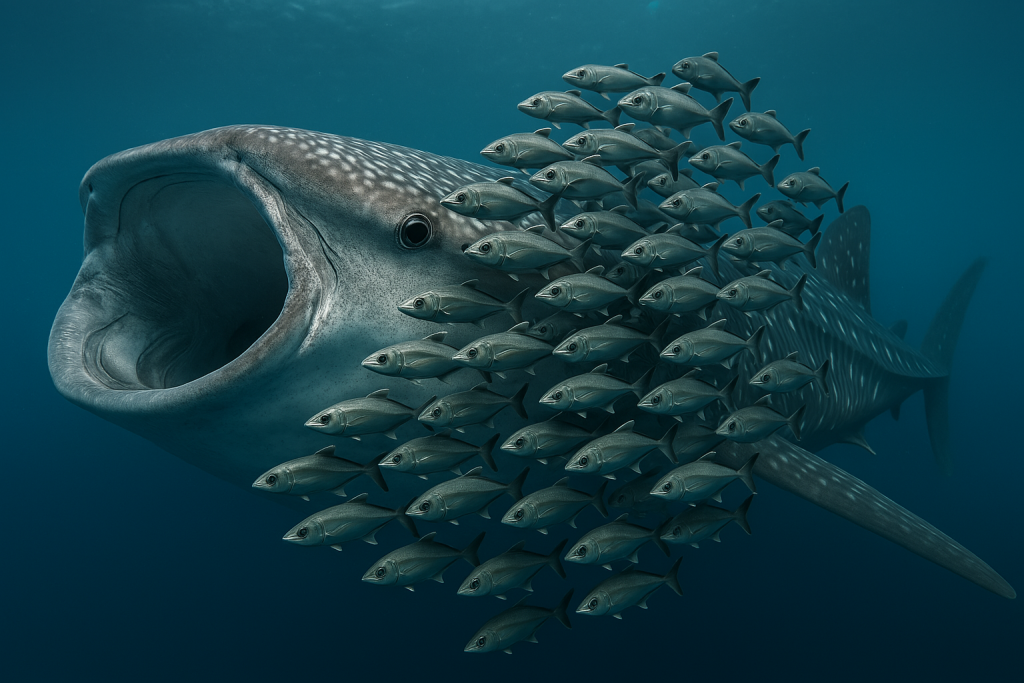蟋蟀——若要說哪種動物最能代表秋天,那一定非它莫屬。 早在甲骨文裏,象形的“秋”字就是畫了一隻蟋蟀,後來才演變成今天的“秋”。 而“秋”字的發音,可能也與蟋蟀的叫聲脫不開關係。 畢竟當蟋蟀鳴唱時,聽起來像“秋秋秋秋秋”,所以才被喚作“蛐蛐”。 由此可推想,古人或許正是因為聽到“蛐蛐”開始叫,才知道秋天到了。 可事實上,蟋蟀並不是只在秋天才出現——它們其實春天就已孵化,只是在我國北方,標誌性的鳴叫往往從八月份(也就是立秋之後)才逐漸多起來,然後差不多會叫上一整個秋天。 也正因為如此,在古人看來,蟋蟀就成了最能代表秋天的象徵。
那麼蟋蟀的存在感為何如此强烈? 這和它們選擇的鳴叫時機也有關係。 它們大多在夜晚最為活躍,尤其在郊區或鄉村這些相對安靜的地方,深夜靜下來後,你可能聽到的主要聲響就是蟋蟀的叫聲。 如果你不信,可以走到窗邊聽聽看; 反正我這兒幾乎整夜都被它們的蟲鳴包圍,這聲音可謂秋夜裏最具代表性的旋律,一聽就讓人倍感秋意。
由於蟋蟀偏愛在秋天“高歌”,也讓它有了一個俗稱叫“促織”。 還有句俗語:“促織鳴,懶婦驚。”意思是說秋意漸凉,蟋蟀的鳴聲聽起來像織布機在響,好似在催促各家主婦趕快忙活,準備為冬天織衣服。 這些都足以說明蟋蟀與秋天之間的深厚淵源。 除了象徵秋天以外,圍繞蟋蟀也衍生出許多有趣的典故,比如鬥蟋蟀——這一活動自古代起一直流行至今,還有“蟋蟀叫聲竟引發了神秘事件”之類的離奇說法。
譬如從2016年開始,美國外交官在古巴哈瓦那遭遇所謂的“聲波攻擊”,險些影響國際關係。 有人推測,這起懸案的元兇或許是一種印第短尾蟋蟀的高頻鳴叫。 聯合國糧農組織則看好蟋蟀在未來糧食安全中的作用,認為“蟋蟀能不能吃、好不好吃”是個全球性議題,這些都值得討論。 所以今天,就讓我們好好聊聊蟋蟀的傳奇故事。
說到常見的昆蟲,和蟋蟀關係最近的是“樓姑”,它們同屬蟋蟀下目; 稍微遠一點的是“中絲下目”,也就是蟈蟈和紡織娘——它們與蟋蟀共同組成“劍尾亞目”。 所謂“劍尾”,指的是它們雌蟲大多擁有一根顯眼的產卵器,看起來像寶劍一樣,用來插入土中產卵; 再遠一些的親戚則是“錐尾亞目”裏的蝗蟲。 和蟋蟀相比,蝗蟲沒有那把“寶劍”,頭上的觸角又短又粗,而蟋蟀等的觸角更細更長,這也是個明顯的區別。 總之,蟋蟀、蟈蟈、紡織娘、蝗蟲,這幾比特就是昆蟲綱直翅目裏的代表物種。 咱們今天的重點,當然還是蟋蟀。
全世界的蟋蟀約有900多種,溫帶和熱帶分佈都很廣,尤其熱帶地區種類最豐富,緯度越高、氣溫越低的地方,蟋蟀就相對稀少。 世界上最大的蟋蟀體長能達到五釐米,長相十分兇悍,果然“强者恒强”,據說來自臥虎藏龍的非洲,學名寫作“brruch choppest”,它們會挖洞,把自己和產卵都安置在洞裏,安全隱蔽。 亞洲這邊也有一些大塊頭,體長可達四釐米,屬於“大蟋屬”,同樣是挖洞生活。 不過大蟋蟀的叫聲比較獨特,帶有拉長音,聽起來有點像蟬鳴。
大多數蟋蟀過著獨居生活,通常夜晚較為活躍; 白天它們潜藏在石縫、落葉、草叢下,或者在自挖的洞穴裏不輕易露面,等夜幕降臨再外出覓食。 它們的食性很雜,什麼嫩草嫩葉、花朵果實,或其他昆蟲的蟲卵幼蟲,都能成為“盤中餐”。 等到若蟲經歷最後一次蛻皮後,就會羽化變成成蟲,長出翅膀。 當然,多數蟋蟀的翅膀並非用來飛,而是用來“演奏”的——它們的叫聲中可是大有文章。
關於蟋蟀晚上的鳴唱,有人會覺得吵,但對更多人而言,其實並不算難以忍受,甚至還能帶來幾分愜意。 比如唐朝開元、天寶年間的記載中,就提到當時有些人喜歡把蟋蟀裝進小金籠,置於枕邊,夜晚聽著它的蟲鳴入眠。 據說唐太宗李世民也曾靠這聲音治好了失眠。 可見對一部分人來說,蟋蟀的叫聲就像白噪音,越聽越能安神入睡。 當然,這種“助眠”效果,並非對所有人都見效——但是,有一樣東西肯定能讓你更好地享受睡眠,那就是一個舒適的床墊。
說來巧,最近我正好體驗了一款不錯的床墊,想推薦給大家。 不得不說,我第一次見到還能打包進箱子裏運輸的床墊,自己一個或兩個人就能輕鬆搬動。 包裝裏有一個很巧妙的缺口,暗藏刀片,讓你安全又方便地拆封。 床墊邊緣還貼心地設計了把手,兩個人搬運起來更輕鬆。
這款床墊的品牌是德國艾瑪床墊(由艾拉代言),在全球範圍內銷量非常可觀,全球已售出一千多萬件商品,並在世界各地斬獲超過60項大獎,可見其品牌實力不容小覷。 我當時先試睡了一陣子,想看看它的實際效果,再來和大家分享。
好了,各位,這款Hybrid獨立筒床墊,我已經試用了一個多月了。 老實說,剛開始我還擔心它會不會太軟——因為第一天我坐在床沿時,感覺很容易往下陷。 然而真正躺下去睡覺時,這種疑慮就消除了。 它的硬度其實相當不錯,支撐性很好,屬於睡感偏硬的床墊。 對我個人而言,正好達到了不軟不硬的平衡點。
這款床墊是德國艾瑪床墊的Hybrid獨立筒系列,採用獨立筒+記憶棉的五層混合設計。 獨立筒的好處在於抗干擾——我夜裡翻身或者起床,也不會影響到旁邊的夫人,讓彼此都能安穩入眠。 再加上記憶棉,能實現人體工學的設計,讓你側躺時脊柱保持一條直線,自然就更放鬆,對休息頗為有利。 另外,德國品質的耐久度也值得信賴——每一款床墊都經過嚴苛測試,質量絕對有保障。 廠家還提供了十年質保,顯然是對自家產品信心滿滿。
有了好床墊,枕頭也得跟上。** 德國艾瑪的經典記憶枕**就很不錯,尤其是它採用三層記憶棉,可根據個人喜好調節高度,這點非常貼心。 我也要再安利個好物:超實用的防水抗敏保潔墊,內含益生菌保護層,可减少89.3%的塵蟎過敏源,而且可以直接丟進洗衣機水洗,就算不小心弄髒,也毫無壓力,非常方便。
如果你對德國艾瑪的床墊和枕頭感興趣,現在正是入手好時機。 官方提供了很多實惠服務:100天試睡、全臺免費送貨上門、10年質保,還有分期付款,每天只要3塊錢就能睡上歐洲品質的好床墊。 尤其現在趕上早鳥雙十一特別優惠,最低5折。 大家可以通過諮詢欄裏的連結進入購買頁面,然後輸入我的專屬優惠碼“老肉10”,就能享受全品項9折,再疊加官網原有優惠,真的挺划算。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緊機會下手。
話歸正傳,咱們回到蟋蟀身上。 2016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美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出現了一系列奇怪的症狀,比如耳鳴、頭暈、頭痛,甚至聽力喪失等,仿佛遭受了刺耳譟音“聲波攻擊”,後來被稱為“哈瓦那併發症”。 其他國家也出現過類似報告,但幾乎都是美國政府人員中招。 到2021年,這類病例已有幾百例,十分詭異。 美國方面第一反應就是“敵對勢力”在搗鬼,猜測可能是某種聲波武器,於是請中央情報局等部門調查,結果並未發現任何證據,反倒排除了人為作祟的可能。
後來,有一種推測認為,除了當事人的心理和健康因素外,真正“元兇”也許是一種“印第短尾蟋蟀”。 它們的鳴叫頻率特別高,約6.9千赫茲,聽起來確實尖銳刺耳,類似聲波攻擊。 我自己試著聽了十幾秒,就覺得腦袋有點發脹。 如果只有美國人出現症狀,這一點尚且不好解釋,囙此“哈瓦那併發症”的成因和真實性仍存疑,但有人將其歸咎於蟋蟀也不無道理。
不過,平時我們聽到的大多數蟋蟀,聲音並沒那麼高頻,反而相對清脆可聽。 那麼蟋蟀是怎麼發聲的呢? 奧秘就在它們的前翅上。 那對前翅相對硬質,就像兩片“硬化膜”,其中一片帶有齒條狀結構,另一片邊緣充當刮板。 當蟋蟀抖動翅膀時,刮板就在齒條上“咯咯”地來回刮,聲音也被“硬化膜”放大,於是變得響亮無比。
此外,“蟋蟀叫聲能當溫度計”這一說法也挺有意思。 美國物理學家阿莫斯·多貝爾發現,當地有種“雪樹蟋蟀”的鳴叫頻率和溫度關係密切:溫度越高,叫得越快。 他還總結了一個公式——讓這類蟋蟀鳴叫60秒的次數加上30,再除以7,就大致等於當時攝氏溫度,誤差不超過1℃。 不過不同蟋蟀種類肯定不一樣,但你或許也發現,天氣越凉,它們的叫聲往往越慢。 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觀察對比一下。
說到蟋蟀,不得不提“鬥蟋蟀”。 與鬥牛、鬥雞這些容易導致流血的活動不同,蟋蟀一旦打不過就會弃賽逃跑,一般不至於受重傷。 囙此在動物保護層面,鬥蟋蟀並不像鬥雞那麼富有爭議,只要不賭博,更多時候算是一種相對溫和的娛樂。 據說鬥蟋蟀始於唐朝,之後在歷代傳承下去。 最初是權貴們的玩物,後來平民百姓也加入其中,畢竟蟋蟀隨處可見,要玩就能玩。 但要想鬥得好、鬥得贏,裡面門道可多了。
南宋宰相賈似道就沉迷於此,還寫了本書《促織經》,詳述如何挑選、飼養、比賽蟋蟀,成為全球首部研究蟋蟀的專著。 從中也能看出鬥蟋蟀的三大關鍵:挑蟲、養蟲、鬥蟲。 先說挑蟋蟀,就得提到“產優質戰蟲”的山東甯陽、寧津、樂陵等地,據說當地水土環境格外適合蟋蟀生長。 行家們每到八月就會蜂擁而至,光甯陽縣一年就能來十幾萬“蟲客”,場面極其火爆。
好的蟋蟀講究“大頭、粗腿、須直、鳴聲渾厚如鐘”,這樣的上品價錢自然不菲。 動輒上千都不奇怪,個別極品甚至能賣到上萬。 2015年還聽說出過一隻賣5萬的“天價蟲”。 於是當地很多農戶靠賣蟋蟀致富,“一隻蛐蛐兒換三頭牛”的說法正是由此而來。 可買到好蟲後,想要調養好更是學問:單靠普通糧食飼料還不够,為了讓蟋蟀更勇猛,有人會喂蝦肉、蟹肉,甚至海參、鹿茸……各種獨家秘方層出不窮,真是讓人嘆服這種鑽研精神。
等到了要比賽的日子,一般正規賽會要求提前幾天統一收蟲,由組委會集中飼養,防止有人“偷喂興奮劑”。 分組對陣時,要用極為精密的稱(可稱黃金的那種)來給蟋蟀稱重,兩隻重量差在20毫克以內才能對決,確保公平。 正式開戰後,判定勝負的規則也非常細緻:如果兩隻蟋蟀互相撕咬,直到一方逃跑、另一方鳴叫,這就算分出了勝負。 但什麼叫贏半局、贏一局,還有“雙爆局”之類的規定,各種條文林林總總,感興趣可自行查閱。 我在此要提醒的是:鬥蟋蟀終歸只是娛樂,若太過沉迷,就失去了樂趣的本意。
2017年,聯合國糧農組織在談及糧食安全時,曾提出昆蟲蛋白對養活不斷增長的人口至關重要,其中蟋蟀就被認為是一大希望。 原因在於它們的飼料轉化率極高,大約是牛的五倍,再考慮到高效繁殖率,綜合效率能比牛高出15到20倍,確實非常可觀。 這樣看來,養殖蟋蟀來獲取蛋白,經濟又環保,理論上很值得推廣。 然而,從現實來看,吃蟋蟀現時並未普及,主要是許多地區的飲食習慣不包含這一項,只有少數非洲國家和東南亞,如高棉、老撾、泰國等,才會把油炸蟋蟀當作佐酒小吃。 哪怕在中國,螞蚱、知了猴、蠍子、蠶蛹都有人吃,唯獨蟋蟀的“上桌率”不算高。
日本這幾年在蟋蟀養殖上花了不少功夫,科技也漸趨成熟,但在市場推廣上依舊不理想,畢竟福斯對昆蟲食材的接受度仍相對有限。 也許更現實的做法是先將蟋蟀製成蛋白粉,再添加到各種食品裏——只要人們不去直觀地看見或接觸,心理上可能更能接受。
總而言之,關於蟋蟀的話題可謂包羅萬象:它能喚起秋天的意境,能成為一項古老的娛樂管道,也能牽扯到國際關係,甚至潜藏著“未來糧食”的可能性。 無論如何,秋夜聽著“秋秋秋”的蟋蟀鳴叫,仿佛又把我們帶回那個悠遠寧靜、蟲聲唧唧的時節。 秋意漸濃,不妨慢下脚步,聆聽蟋蟀的低語——也許你會發現,秋天因為它們的歌聲而愈發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