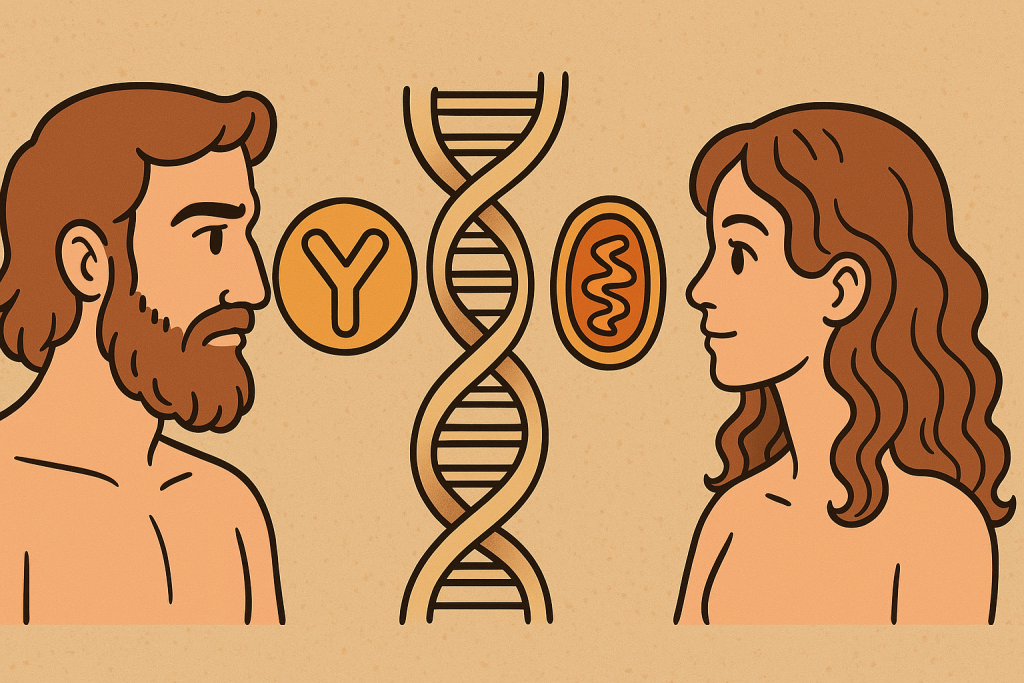小麥,堪稱全球種植面積最廣的糧食作物——全世界一共種了兩億多公頃,幾乎相當於把中國約四分之一的土地都鋪滿了麥田,規模可謂驚人。 若以產量來算,小麥年產約八億噸,僅次於玉米的十二億噸。 不過,玉米當中很大一部分並非直接供人食用,而是用作飼料或製造乙醇等; 相比之下,小麥幾乎全部都變成了人類的口糧。 要知道,人類每天從食物中攝取的總熱量裏,約有五分之一都來自小麥,可見它對我們的“飽腹”貢獻有多麼重要。
除此之外,小麥的普及範圍也相當廣。 即便一個地區並非小麥產區,人們也會吃到通過進口而來的小麥製品。 你想想:就算有人從未嘗過饅頭,也大多吃過麵包; 就算麵包都沒吃過,麵條總該試過吧? 再加上餅乾、蛋糕、大餅、包子、漢堡、披薩等各種花樣美食,小麥真是無所不在。 所以,從貿易量來看,小麥在全球糧食作物中也高居前列——大約四分之一的小麥每年(差不多兩億噸)都在國際市場上流通,足見其地位之重要。
小麥之所以能如此“稱霸”,背後有段非常傳奇的過程。 畢竟,它的祖先不過是土耳其那一帶一小片區域裏毫不起眼的野草,別處根本沒有。 後來,小麥的基因組經歷了哪些神奇變化,它又如何邁向“征服世界”的征途,著實值得深入探究。 再者,與玉米、水稻等糧食作物相比,小麥還含有一種相當獨特的物質,也正因如此,它成了無可替代的食物。 然而,也正是因為這物質,小麥竟然成了“陰謀論”的熱門主角:有人說它會讓人上癮,是“殺人無數”的慢性毒藥,甚至聲稱已知疾病中有七至八成是小麥惹的禍,簡直誇張至極。
這些驚悚的說法究竟從何而來? 他們的“理論依據”又是什麼? 這正是今天要探討的話題。 不過在此之前,先提醒大家:如果喜歡這個頻道,別忘了訂閱、點贊或分享給朋友哦。 說起來,在之前那期聊地瓜的時候,提到地瓜基因組是六倍體,由二倍體祖先與四倍體祖先雜交而來。 有觀眾就問:二倍體和四倍體雜交,不該出現三倍體嗎? 怎麼變成“2+4=6”了呢? 其實,在植物界,這種情況並不少見——據說大約三分之一的植物都經歷過類似的染色體疊加。
原因在於,有些未知的偶然因素會導致胚胎未能正常減數分裂,而是直接結合,繼而誕生的後代恰好具有生存優勢,沒有被自然淘汰,就出現了多倍體植物。 而本期的主角——小麥,正是典型的多倍體,與地瓜一樣是六倍體,基因型記作A A B B D D,意即它擁有六套染色體。 不過,比地瓜更複雜的是,小麥的祖先“譜系”可謂錯綜。 地瓜的祖先至少還算同屬一個屬,而小麥在生物學分類上歸於禾本科的小麥屬,卻牽扯進了更多變數。
從基因素源來看,小麥屬大約誕生於250萬年前,最初的祖先是普通的二倍體小麥。 當時與之分化的另一個屬叫“山羊草屬”,基本屬於野草,很早就與小麥屬分道揚鑣。 又過了約100萬年,小麥屬分化出了兩個二倍體物種——“烏拉爾圖小麥”和“伊粒小麥”。 這裡要注意,“伊粒小麥”並不是“一粒小麥”,它只是野生小麥的一種名稱。 要區分這點,還得先知道:小麥的麥穗能分出許多“小穗”,輕輕一掰就能取下,而每個小穗中麥粒的數量,視品種而异。
現代小麥通常一個小穗能有兩到三粒麥子,而最原始的“一粒小麥”每個小穗裏就只有一粒,囙此才得名“一粒小麥”。 大約五十萬年前,小麥屬的祖先之一——烏拉爾圖小麥,瞄上了山羊草屬中一種雜草“斯佩爾托山羊草”,二者雜交誕生了“二粒小麥”。 這就是四倍體小麥,基因型為A A B B,其中B基因來自山羊草。 很多人誤以為“一粒小麥”雜交出了“二粒小麥”,其實不然——“二粒小麥”的祖先正是烏拉爾圖小麥。 早在五十萬年前,自然狀態的野生小麥就已經獲得了A A B B型。 那麼剩下的D D又是從哪裡來的? 別急,我們按時間順序來看。
接下來,人類粉墨登場。 考古發現,人類最早食用小麥的證據可追溯到約3.2萬年前,比農業革命還早了近兩萬年。 那時人們還是狩獵採集者,只能零星獲取野生小麥,數量有限,並非主食。 直到約1.3萬年前,人類迎來了“第一次農業革命”——末次冰期接近尾聲時,歐洲氣溫逐步回升,可突然之間,又發生了“新仙女木事件”:北半球氣溫在短短幾年內猛跌五度以上,北極冰川向南擴張,導致北方環境迅速惡化,大量動植物無法生存。 歐洲的人群不得不一路南遷,抵達新月沃地尋找食物。 但隨著人口激增,當地的野生資源也不够吃,便催生了對“種植”的需求。 恰好新月沃地分佈著野生小麥,於是人類開始馴化它。
最早被馴化的,是前面提到的“一粒小麥”(二倍體),隨後又是“二粒小麥”(四倍體)。 一萬年前,新月沃地農業初興之時,主要種的就是這兩種。 由於有了穩定可種植的小麥,食物供應越來越充足,人口大幅增長,許多人學會了耕種,開始定居生活。 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也囙此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村莊,為蘇美爾文明的誕生奠定了基礎,其意義舉足輕重。 那人類在馴化小麥時,到底改變了哪些特徵呢?
首先,最直觀的變化是麥粒和穗頭變得更大,提高了產量。 其次,野生小麥的麥穗十分脆弱,一碰就碎,散落成帶殼、帶芒的種子,這是它利用風力傳播的管道。 但對人類而言,過於易碎的麥穗並不友好,所以馴化後的小麥穗軸更加堅固,便於收穫。
此外,野生小麥還有個有趣現象:它竟能“自動播種”。 據德國研究團隊在2007年發表的結果顯示,野生小麥的兩根麥芒在風力傳播時,就像小傘一樣幫助種子飄得更遠; 更神奇的是,這對麥芒還能在夜晚高濕度時合攏、白天乾燥時張開。 這個持續“張合”的運動,再配合麥芒上的倒刺,會把種子一點一點往土裏推進,最終就把自己埋進了泥土。 可一旦被人類馴化,這些神通自然就不再保留——一方面,馴化品種的穗軸不易散落; 另一方面,人類自會幫它播種。 不過,這個階段的馴化小麥雖然在新月沃地稱得上“主力”,卻還不足以走向世界。 它還缺少一樣關鍵本事。
為什麼它一開始無法在全球溫帶地區“漫步”? 因為新月沃地是典型的地中海氣候:夏季炎熱乾燥,冬季溫暖多雨,小麥的“妙招”就是秋冬發芽,冬春時快速生長,在入夏前完成結籽,以種子度過酷暑。 到了溫帶季風區,例如中國北方,冬季寒冷乾燥,萬物蕭條,小麥很難越冬。 可後來它竟然成功“闖關”了世界各地,這就要多虧小麥基因組裏的D基因。 約8000年前,裡海沿岸栽培的二粒小麥也像它的“前輩”一樣,與“節節山羊草”(又稱“節節麥”)雜交,誕生了現在最常見的六倍體——普通小麥(A A B B D D)。 正是“節節麥”貢獻的D基因,讓小麥擁有了更强的抗寒能力,適應力大增,足以向更廣闊的區域擴張。
小麥大概在5000年前傳入中國,由中亞先到新疆,再向北方擴散。 當時北方主糧是黍米(即小米),可小麥產量高、適合當主食,很快就被接受。 到商周時期,從河西走廊到黃海之濱,黃河中下游已普遍種植小麥,甚至在《論語》提到的“五穀”中,也包含了這個“外來戶”。 小麥對中國古代的意義不僅僅是新增一種糧食,它具有重大戰畧價值。 傳統作物大多春種秋收,冬天田地荒著不說,秋收後的糧食通常撐不到來年夏季,饑荒頻發。 有了冬小麥(秋種夏收),就能最大化利用冬季土地,實現秋收前多一輪產出,一舉緩解了夏季缺糧難題。 囙此,小麥對中國農業發展功不可沒。 當然,飲食習慣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變的,直到唐宋時期,小麥才真正超過小米地位,這與北方居民日益青睞麵食密不可分。 後來,中原地區逐漸以麵食為主,如今已對小麥“愛不釋口”。 世界其他地方也不例外,各類麵食層出不窮,既能果腹,又豐富了人們的餐桌,這一點任何別的作物都很難企及。 但偏偏就是這樣熟悉的小麥,也曾被扯進一場“陰謀論”之中。
我們都知道,大米和小麥是人類最主要的兩種口糧,但吃法有明顯區別:大米洗淨燜熟即可食用,而小麥太硬,需要先磨成麵粉再加水和麵,或許還要發酵,看似麻煩。 然而正是這道繁瑣的工序,讓小麥可以變身為形形色色的麵食,彰顯出它的獨到之處。 為什麼大米做不到? 關鍵在於小麥含有一種特殊蛋白質——麩質(俗稱“麵筋”)。 大麥、燕麥等也含有麩質蛋白,它起到“黏合劑”的作用,一遇到水就形成一張“網”,緊緊鎖住澱粉,既使麵團能保持形狀,還讓口感更筋道。
人類歷史上最早的麵食,正是麵包。 考古學家推測,或許在1.4萬年前,人類就出現了最初的麵包雛形; 而真正成熟的發酵麵包,則是在發現酵母菌後才誕生。 至於酵母菌與麵包起源的精彩故事,就先按下不錶,我打算在會員專享內容裏展開。 其實會員頻道還有很多優質話題,想深入瞭解的朋友,只需半杯奶茶的價錢就能加入,絕對是全網最低價,歡迎支持。
回到小麥和麩質本身,科學界研究已久,人類幾千年來一直吃得好好的。 但在2011年,卻有人突然宣稱,小麥麩質暗藏“陰謀”,必須戒掉! 這位美國心臟病專家名叫威廉·戴維斯,他在當年出版了《Wheat Belly》一書,認定小麥是一種會令人上癮的慢性毒藥,並且聲稱70%到80%的疾病都和小麥有關,這聽起來相當可怕。 不管是肥胖、癌症,書裡似乎都能把鍋甩給小麥,仿佛只有徹底不吃小麥才是“健康之道”。
令人大跌眼鏡的是,這本書問世後僅一個月,就躍上暢銷書排行榜,並連登榜單長達一百周之久,影響甚廣。 許多娛樂藝員、體育明星都成了大衛斯的粉絲,至少數百萬人乃至上千萬人開始相信這一說法,表示要“戒麥”。 大衛斯最巧妙的地方在於,他並沒有“一杆子打死”所有小麥——否則人類吃了幾千年,早該發現問題。 他把矛頭對準“現代小麥”,尤其是1960年代以後出現的“轉基因怪物”,聲稱這些新品種正在大規模危害人類。
例如,他舉例說過去小麥長得高,可到人胸口或肩膀; 如今“改造”後的小麥只到大腿,正因這“基因修改”,小麥才成了“慢性毒藥”,已不復從前。 那這些說法可信嗎? 面對這股轟動的“小麥陰謀論”,眾多科學家紛紛站出來予以反駁,指出大衛斯提供的種種“科學證據”裏存在自相矛盾或主觀臆測。
比如,小麥專家比對了自1800年以來不同時期的小麥樣本,發現它們在蛋白質結構、營養成分等方面差异微乎其微,根本沒有導致疾病的重大變異。 至於小麥“變矮”,壓根也不存在“陰謀”——早在一千多年前,日本、韓國就有一種編號為“農林10號”的矮稈品種。 後來生物學家諾曼·布勞格將它與墨西哥小麥雜交,培育出新品種,大幅提高了產量,抗倒伏、防銹病。 上世紀六十年代,印度和巴基斯坦種植後,小麥產量翻了一倍,讓至少十億人免於饑餓。 布勞格囙此在1970年獲諾貝爾和平獎,可大衛斯卻把這種讓無數人脫離饑餓的“矮稈小麥”說成“毒藥”,實在讓人無言以對。
當然,小麥確實跟少數疾病有關,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麩質過敏症和乳糜瀉。 對於這些患者,食用含麩質的小麥會帶來腸胃不適及其他症狀,確實應當謹慎。 但這只占很小的人群,絕大多數人吃小麥並無任何問題。 像我們天天吃麵食,若真有70%到80%的疾病都是小麥導致,那醫院豈不是早就人滿為患?
所以說,“小麥陰謀論”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大衛斯巧舌如簧、營造恐慌心理的結果。 他把故事講得繪聲繪色,難免有人輕信。 不過,究竟真相如何,還是要結合科學研究和獨立思考,切莫別人說什麼就一股腦兒相信。
以上就是小麥的傳奇故事:從默默無聞的野草到全球主糧,從改變人類命運的農業革命“主角”,到被貼上“慢性毒藥”的陰謀論標籤,足見小麥在人類歷史上扮演了多麼關鍵又多麼多變的角色。 而對於那些坊間傳言,我們更需要保持冷靜、多方求證,以科學態度看待這株人類餐桌上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