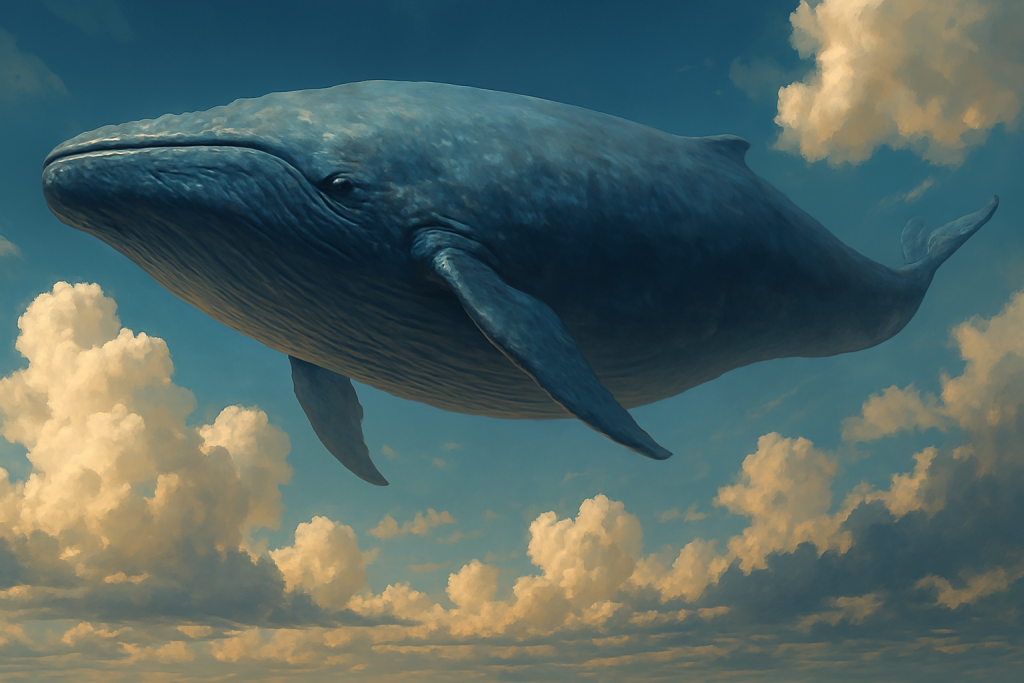你真的瞭解鮑魚嗎? 這種美味的海洋生物不僅能封锁海膽氾濫,竟然還在某些地方捲入了毒品貿易! 你又知不知道它的腦袋究竟長什麼樣?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揭開鮑魚那不為人知的傳奇故事。
鮑魚,大多數人都不陌生,作為一種海鮮食材,它在中、日、韓等國家的人氣向來居高不下,而世界上消費鮑魚最多的地區也正是東亞。 其實,考古學家告訴我們,早在智人剛“行走江湖”之時,就已經開始品嘗鮑魚了:在非洲大陸最南端開普敦往東約三百公里的布隆博斯洞窟,考古證據可追溯到十萬年前,這裡留下了先民吃剩的鮑魚殼。 又如加州海岸的海峽群島,也能找到一萬兩千年前人類食用鮑魚的遺跡,時間和地點都與人類向美洲擴散的主流理論相符。

囙此,鮑魚自古以來就是人類的“老朋友”。 非洲高山族、紐西蘭的毛利人以及美洲高山族至今還保留著吃鮑魚的傳統,只是整體人口基數小,鮑魚消費量並不大。 放眼全世界,東亞,尤其是中國,仍然是吃鮑魚最“兇猛”的區域。 可我們真的認識鮑魚嗎? 或許你潜水時見過活的鮑魚,在市場上也見過幹鮑、凍鮑等各種處理後的產品,但對於它的身體結構,尤其是那一顆“腦袋”究竟長啥樣,恐怕許多人都沒仔細留意過。
除了美食身份,鮑魚在海洋生態中也扮演著關鍵角色,甚至還牽扯進了毒品貿易。 今天,讓我們深入瞭解這看似低調卻故事多多的鮑魚。
一、鮑魚的奇特結構:只有一片殼的海螺“兄弟”
我們都知道,鮑魚只擁有一片貝殼,看上去有些像一般貝類的“單片殼”。 普通雙殼貝類(如蛤蜊)遇到危險時,會合上兩片殼自我防禦; 鮑魚卻只能把自己緊緊吸在岩石上,靠强大的吸力封住殼口。 日本甚至有一句俗語形容它:“easor no b諾卡塔姆米”,意思是其他貝類都是“成雙成對”,可鮑魚只能一面死命往岩石上貼,形象地描述了它的處境。
其實,鮑魚與雙殼類完全不是一回事,它屬於腹足綱,也就是“海螺家族”。 可以這麼理解:如果把海螺的開口無限放大,再將螺殼從肩部整個壓扁,就變成了鮑魚殼。 囙此,你依然能在鮑魚殼上找到類似海螺螺線的痕迹。 如今,世界上已知的鮑魚約有六十種,最小的成體只有兩三釐米大,最大的加州紅鮑卻能長到三十多釐米。
鮑魚邊緣看起來就像一個耳廓,中間略微凹陷,故又有人叫它“海耳”。 在西太平洋區域,還有一種“驢耳鮑”,又細又長,更像人的耳朵。 不過,大多數鮑魚還是近似橢圓。 它們的殼色、花紋、質地五花八門,這與生活環境直接相關——為了隱蔽,它們通常會讓外觀與棲息的岩石儘量相似。 可不論顏色如何變化,殼面都有一排排孔狀的排孔,看起來就像一連串小火山口。 這些排孔會隨著鮑魚的生長不斷更迭:新孔生成,舊孔封閉。 最終,只有少數幾個保持暢通,用於呼吸、排泄和排卵,讓它們幾乎不必離開岩石就能完成各種生理活動。
說到身體部分,很多人只注意到那塊可以吃的大肌肉,卻忽略了鮑魚其實也有頭——擁有嘴巴、一對眼睛,以及長在頭部的觸鬚。 只是它那“頭部”的存在感極低,完全被發達的肌肉給搶了風頭。 我們平常說“一頭、兩頭、三頭”的鮑魚,指的是它的大小,卻很少有人想過“它的頭到底啥樣”。 囙此,如果沒真正見過它的腦袋,恐怕也不能算是真的認識鮑魚。
二、與海膽的生態糾葛:拯救海帶森林的“厚道幫手”
此前我們曾聊過海膽的氾濫,無論是在加州還是塔斯馬尼亞,都曾出現過海膽數量暴增、肆虐海帶森林(或巨藻林)的現象。 海膽特愛啃食海帶根部,只要幾口就能讓幾十米長的海帶飄走、枯死,最終將海底變成“海膽荒漠”。 人們常把海膽氾濫怪罪於其天敵的减少,比如塔斯馬尼亞的岩龍蝦、加州的海獺。 但科學家發現,鮑魚也在其中扮演了一比特重要角色。
以加州為例:從1741年到1911年,人類瘋狂捕殺海獺,使其數量一度驟減。 然而,奇怪的是,當海獺最少時,卻並沒有出現海膽成灾的情况。 原因在於另一種海獺美食——鮑魚——數量逐漸增多,鮑魚同樣會吃海帶,但它們只吃沉在海底的葉子和碎片,不會像海膽那樣把海帶“斬草除根”。 它們吃得不多又不會浪費,海帶生長速度也快,自然相處和諧。 正因如此,海膽當時沒什麼機會紮根壯大。
直到1970年代,鮑魚的高經濟價值讓它們在加州遭到瘋狂捕撈,幾乎沒什麼限制。 白鮑、黑鮑、綠鮑、紅鮑等各品種紛紛被撈上來,數量大幅下滑。 隨著鮑魚的减少,海膽忽然空出了生存空間,這才開始氾濫成災。 而且最讓人頭疼的是,海膽過多會陷入“饑餓模式”,它們的性腺萎縮,變得既不好吃又沒經濟價值,沒人願意捕撈,最終任由海膽荒漠越擴越大。
要想恢復海帶森林,除了恢復海獺數量之外,怎麼讓鮑魚回到海底也被列入了研究課題之中。
三、極度瀕危的白鮑:人工繁育的艱難救贖
上世紀70年代對鮑魚的濫捕,最嚴重波及的是白鮑。 白鮑曾在加州到墨西哥的海岸帶數量龐大,保守估計有幾百萬只。 然而到了90年代,僅用二十年,它們的數量就驟減了99%。 雖然加州在1996年開始禁止捕撈,但偷獵一直不斷。 很多潜水愛好者形容,看見白鮑就像看見一張百元大鈔,真要“無動於衷”可並不容易。
如今,野生白鮑的數量估計只有兩千只左右,被列為極度瀕危物種。 更糟糕的是,由於鮑魚是雌雄異體,排卵排精都釋放在水裏,需要足够密度才能順利受精。 以現時白鮑稀少且分散的情况,即便它們壽命可達三十年以上,要在野外繁衍後代幾乎不可能,等同於“功能性滅絕”。 唯一的希望是人工繁育。
為此,加州大學大衛斯分校的伯德加海洋實驗室已研究了十餘年,終於摸索出刺激白鮑排卵、排精的方法,並用特定藻類精心餵養幼鮑,以提高存活率。 截至目前,他們已繁育了數萬只幼鮑,並在2019年10月將第一批白鮑放歸野外。 這一步至關重要。 然而,人工繁育也面臨不少難題:基因多樣性不足會使抗病能力弱,如枯萎併發症就可能大規模致死; 實驗室中長大的鮑魚,防禦天敵的本領欠缺,在野外常常來不及躲避海星、海螺或龍蝦、螃蟹、章魚的捕食。 即使如此,研究人員依然計畫未來每年放歸十萬只白鮑,希望能讓這個物種在野外重新站穩腳跟。
四、南非鮑魚與地下毒品交易:驚人的黑暗鏈條
高品質鮑魚通常會被製成幹鮑。 先將鮑魚蒸熟或煮熟,再烘乾,就成了幹鮑。 很多人認為幹鮑比鮮鮑口感和香氣更勝一籌,而大個頭的“糖心幹鮑”更被奉為極品。 日本幹鮑被視為質量最佳,而緊隨其後的便是南非幹鮑,每年有大量南非幹鮑出口,主要銷往香港。
然而,人們在享用這道美食時,往往不知道它竟與毒品貿易掛鉤。 南非鮑魚的學名是Haliotis midae,只分佈於南非,如今已是瀕危物種。 成年南非鮑可長到二十釐米,殼呈近圓形。 過去,當地漁民捕撈鮑魚一直是謀生手段,但在1990年代,南非政府執行“配額制”,允許有配額的公司規模化捕撈,普通漁民拿不到配額,只能半夜偷偷下海。
鮑魚被偷獵上來後要銷往哪裡? 正規管道顯然行不通,於是黑幫介入。 他們用極低價格向漁民收購偷來的鮑魚,送進地下工廠加工成幹鮑,再賣到香港。 收購價每公斤僅十到四十美元,到香港卻可賣到幾百到上千美元。 利潤之高,使得犯罪集團為了規避現金往來,轉而用毒品或制毒原料來交換鮑魚,形成了暗中操作幾十年的黑色交易鏈。
調查顯示,走私幹鮑仍占南非出口的大頭。 以2015年的數據為例,從南非到香港的幹鮑中,只有33%來自人工養殖,67%來自野生捕撈,而合法配額只占其中的2%,偷獵部分多達65%。 這和其他野生動物走私並無二致,只要有需求就會有犯罪,瀕危物種也囙此不斷遭受打擊。
不過,鮑魚和其他野生動物略有不同之處在於:鮑魚的人工養殖技術已經相當成熟,只要市場能全面轉向養殖鮑魚,野生鮑魚或許能得到保護。
五、養殖鮑魚:最綠色的水產養殖藝員?
其實,鮑魚可能是現今最值得推廣的水產養殖品種。 它們的食物主要就是海帶、海藻,幾乎不需要使用抗生素或激素,對海洋環境的污染極小。 而且海帶、海藻也能進行人工種植,生長極快,足够滿足養殖需求,完全具備“綠色養殖”的潛力。
當然,一些急功近利的養殖者也會額外添加人工飼料或激素來催生長,但從鮑魚本身來看,純天然養殖並非難事。 除了餌料,水溫也是影響鮑魚養殖的重要因素。 以中國常見的皺紋盤鮑為例,它最舒適的水溫在16到22度之間,過高會導致生病或死亡,過低又生長緩慢。 為此,養殖業者普遍採用“南北轉場對養”模式:每年四五月,福建的鮑魚就會被運到山東榮成“避暑”,十一月再回到南方“越冬”。 雖然要付出額外運輸成本,卻能降低死亡率並保證生長速度,十分划算。
現如今,市場上已有約95%的鮑魚來自養殖。 遺憾的是,養殖品種仍較為單一,個頭也普遍不算大,那些大體型的野生極品鮑魚依舊保持一定市場需求。 未來,如何拓展更多品種、提升養殖品質,或許是鮑魚養殖事業的重要方向。 一旦能大規模養殖所有“極品”鮑魚,不但價格會降低,也能减少對野生資源的破壞,讓人們吃得更安心。
鮑魚,一種從遠古時期就與人類相伴的海洋食材,既能維護海洋生態,又因利益鏈牽涉到毒品交易,命運可謂跌宕起伏。 它那“不起眼”的腦袋、强大的吸力肌肉、獨特的排孔,以及在生態系統裏擔當的作用,都值得我們重新審視。 或許,在人們不懈的努力下,有朝一日,我們既能享受更美味、更健康的鮑魚,也能守護這些珍貴的海洋物種和它們所生存的環境。 讓我們一起期待鮑魚的真正“逆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