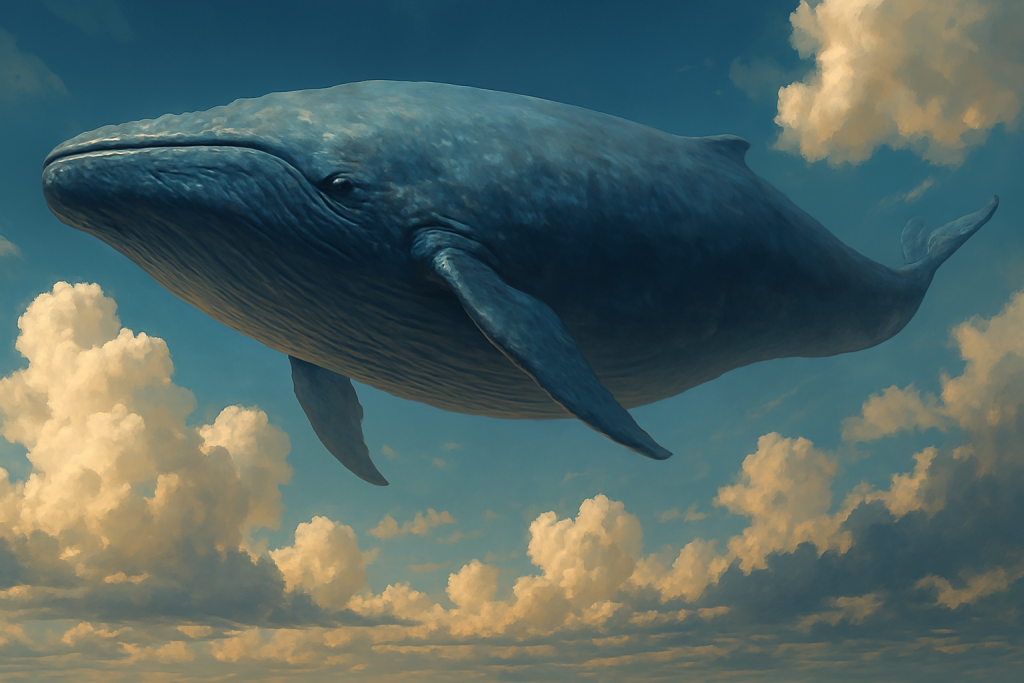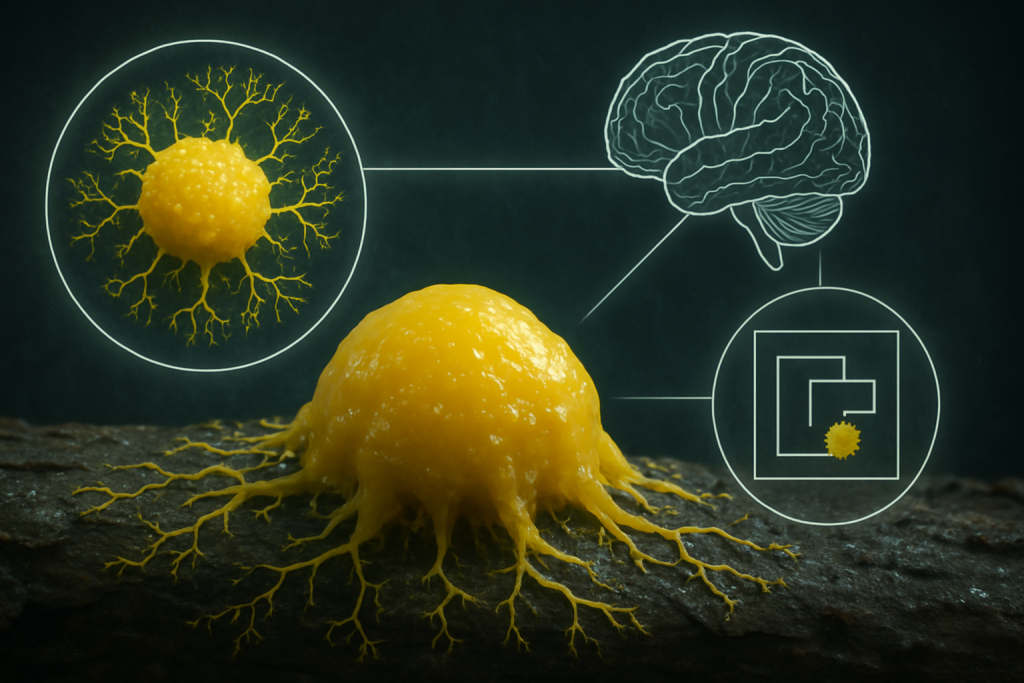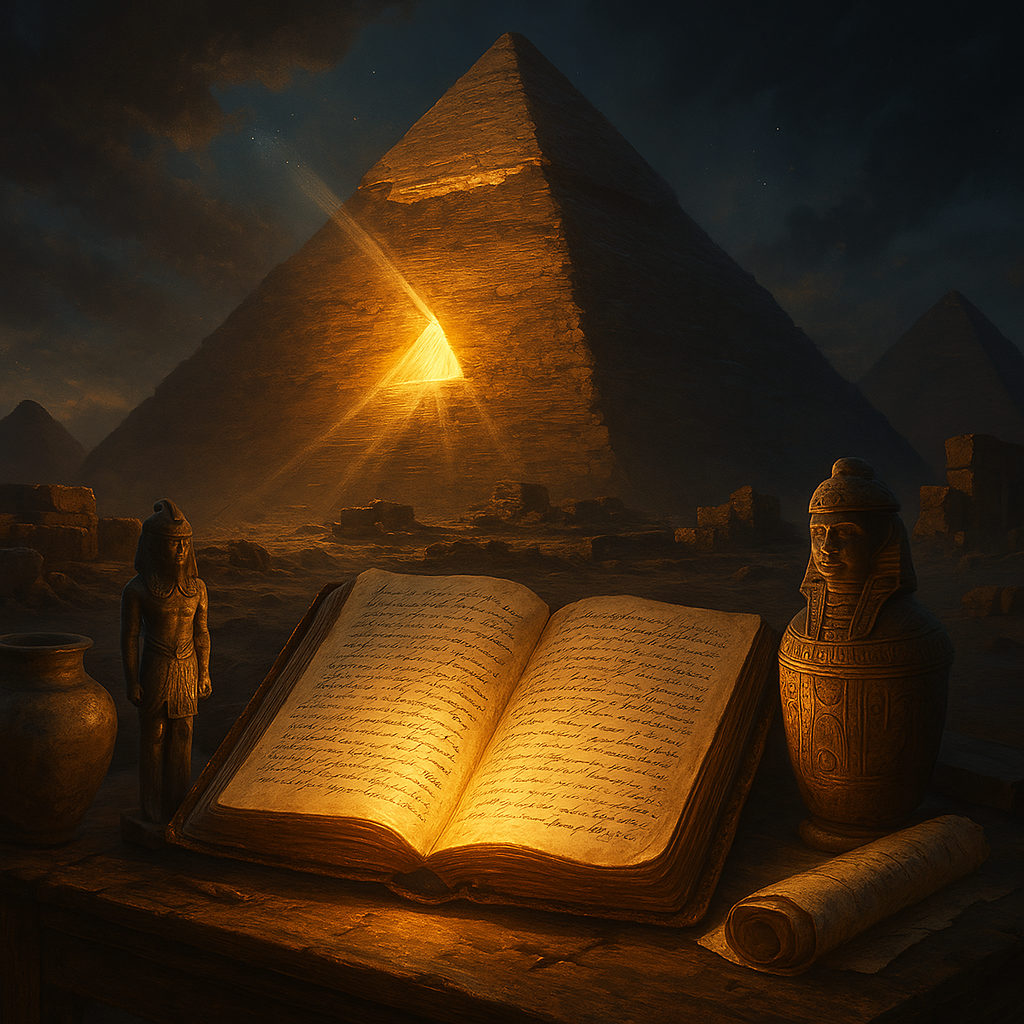當提起地球上最大兩棲動物時,不得不提那神秘而古老的“大鯢”,也常被親切地稱為“娃娃魚”。 你或許在生物課堂上聽說過它們,這些傢伙身體寬厚扁平,尾巴粗大而修長,最大的個體能達到1.8米、體重高達三五十公斤。 若與那些常見的青蛙和蟾蜍相比,大鯢在水族箱中就像一個大麦克般格外引人注目。

在生物學分類中,大鯢隸屬於擁有尾部的隱塞尼克類,現時已知至少存在四個物種:分別是中國大鯢、華南大鯢、日本大鯢和美洲大鯢。 而關於中國大鯢的具體地位仍存在爭議,甚至有人認為它內部可能還會再細分出其他獨立物種。 無論如何,大鯢都是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生物,因為它們的化石記錄可追溯到1.7億年前,與恐龍同時代,堪稱真正的“活化石”,在全球性生物大滅絕中也能見它們英勇存活。
儘管生物學上它們被歸為兩棲動物,但實際上大鯢幾乎終生棲息於水中,很少登上陸地。 它們的行動管道主要以爬行為主:四條短小的腿上長著肉乎乎的爪子,指尖宛如微型吸盤,緊緊抓住濕滑的岩石; 需要緊急逃離時,則會揮動那像船槳一樣的大尾巴,以驚人速度竄出水面。 不過總體來說,慢悠悠地爬行更符合它們的生活節奏。
大鯢雖然擁有進化出肺的能力,但它們在水下生活時鮮少動用這一器官,反而將肺“用”作調節浮力的工具,仿佛魚類的魚膘一樣。 幼年時,它們擁有脖子上的外腮,但長大後外腮逐漸退化,便只能依靠全身那皺巴巴的皮膚進行呼吸。 尤其是身體兩側那明顯如裙擺般的褶皺,其設計正是為了增大換氣面積,儘管皮膚呼吸的效率終究有限。
正因如此,大鯢對水體中的含氧量要求極高,它們只能生存於山間溪流——那種岩石紛呈、水流湍急且水溫不超過20℃的清冽環境。 而水質也必須保持純淨,一旦遭到污染,它們便難以存活,囙此野生大鯢的棲息地如今已屈指可數。
說到食性,幼年的大鯢主要以昆蟲幼蟲和蠕蟲為食,而成年後則轉向小魚、小蝦、小螃蟹等水中小動物。 由於視力欠佳,它們更多依靠敏銳的嗅覺和對水中震動的感知來捕獵。 往往悄無聲息地靠近獵物,待其進入致命吸力範圍時,便突然大張血盆大口,將獵物一吸而盡。 而有趣的是,研究表明它們有時甚至會吞食同類,科學家們推測這可能與激烈的領地爭奪有關,打鬥過程中順手就將對方或對方的幼崽吃掉了。
繁殖方面,大鯢與龍魚有相似之處——雌性一產下數百枚卵後便離場,剩下的孵化和幼崽的照料任務全由雄性承擔。 從產卵數量來看,它們的繁殖能力尚可,但苛刻的棲息要求使得野外存活的數量極為稀少。 現時,包括日本大鯢和美洲大鯢在內的四個物種中,情况都不盡人意,尤其是中國的兩種大鯢已被列為極危級別。 中國政府已為它們建立了十幾個自然保護區,然而野外的大鯢依然十分罕見。
與野外瀕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大鯢的人工養殖卻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 如今,全國養殖場內約有六千萬只大鯢,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陝西秦嶺地區。 養殖目的並非為了野放,而是供應餐桌——大鯢自古以來便被視為美味佳餚,其肉質鮮美,兼具魚肉與蛙肉的獨特風味,囙此深受食客喜愛。 儘管也有嘗試通過人工養殖的放生來新增野生種群數量,但一方面擔心引入疾病,另一方面又怕污染純正的野生基因,故這一舉措尚未大規模推廣。
此外,大鯢在不同地區還擁有各種形形色色的俗稱。 在日本,它們被稱為“大山椒魚”,這一名字甚至為部分火影迷所熟知,據說半藏的通靈獸就是以大山椒魚為藍本,可能與其身上散發的略帶山椒氣味有關。 而美洲的大鯢則被冠以“helbandder地獄狂徒”或“地獄火熔岩”這樣充滿中二氣息的名稱,因其外形兇悍且身上偶露的橙色斑紋宛如岩漿翻滾。 至於在中國,“娃娃魚”這一俗稱究竟從何而來,歷來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是因為它們發出的叫聲酷似嬰兒的哭泣,但事實上,專家指出大鯢並不具備發出如此聲音的器官,更可能是因為它們那圓滾滾的身形和類似嬰兒小胖手的爪子,讓人聯想到可愛的小娃娃。 無論如何,在我看來,當它們被端上餐桌時,何不直呼其名“大鯢”,更顯莊重與獨特。
這就是大鯢,一個既古老又神秘、既可愛又兇猛的史前水中巨獸,它的每一個細節都訴說著大自然的奇迹與生命的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