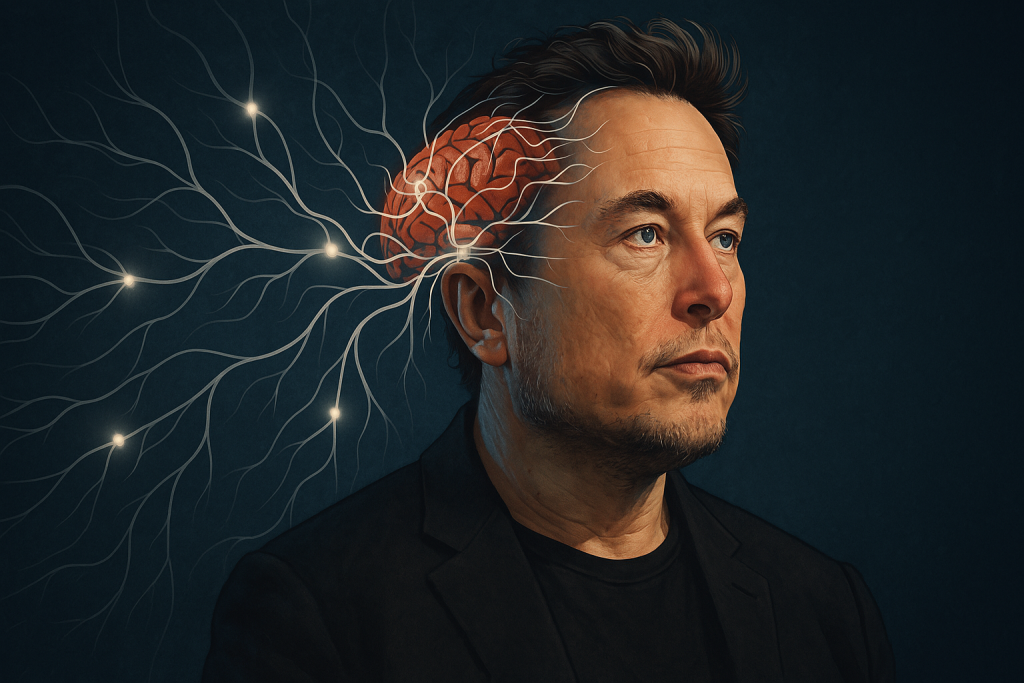海洋中有一種令人驚歎的生物,它既是高效的獵手,又充滿神秘色彩,被譽為“龍的私生子”。 這種動物外形獨特,大家應該都很熟悉,畢竟它就叫海馬。 但許多人可能不知道,海馬實際上是一種魚,而且雖然它看上去動作緩慢、人畜無害,實際上卻擁有令人讚歎的狩獵技巧——只有借助高速攝像才能捕捉到它那出奇制勝的獵食瞬間。 同時,海馬的繁殖管道也足以顛覆你對生育常規的認知:雄性擔任起懷孕和養育後代的重任。 順著這篇文章,你將一窺海馬背後的奧秘。 順帶一提,海馬的學名為Hippocampus,來源於古希臘語,意指“馬”和“海怪”,這正對應了它那似馬又似龍的獨特形象。

希臘神話中描述的那種上半身似馬、下半身似魚的神獸,其實正是海馬的原型。 而在歐洲,有一種說法認為遇難水手的靈魂被困海底時,會化作海馬,將這些迷失的魂靈帶向冥界,使其得以安息。 西方文化中,海馬更是時常以神秘的形象出現,甚至在某些超級英雄電影中,它作為海底王國的坐騎,也充滿了拉風與傳奇色彩。 到了熱衷龍文化的東方,人們望著海馬的身影,仿佛在遠古傳說中看到了龍的影子。 囙此,在中文裏,海馬所屬的科就被稱為“海龍魚科”,其親戚們無論外形還是體態,都與龍頗有幾分相似。
日本的稱謂更是風趣獨到:海馬在日語中被稱為“トンノウ”(tounno),意指“龍的私生子”,暗示它擁有一半的龍血。 這種叫法不僅僅是俗稱,而是在生物學分類中確立的名稱。 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單憑海馬那獨特的外貌,就足以讓人遐想其神秘傳說。 然而,現實中的海馬與這些傳說相比,顯得溫順許多。 首先,它們的體型根本無法勝任“坐騎”的角色。 海洋中約有五十種海馬,體型最大的“澎腹海馬”也不過35釐米高,而體型最小的“薩托米豆”則僅有1.4釐米,遠遠談不上能讓人騎乘。 除了體型微小,海馬的游泳速度也非常緩慢。 作為一條魚,它幾乎失去了所有主要的魚鰭,僅靠後背上那一小塊背鰭在水中掙扎前行。 正因如此,海馬被《吉尼斯世界紀錄》評為世界上游得最慢的魚類,其中特別一種稱作“小海馬”的遊速僅有1.5米每小時。 如此緩慢的速度,使得它在獵食和逃避中形成了獨特的策略。
如果你對海馬是否屬於魚類還存疑慮,分子生物學家已經用基因測序給出了答案——海馬與金槍魚的親緣關係甚至比鮭魚與金槍魚還要近,真正印證了“魚不可貌相”的道理。 儘管海馬保留了一些典型的魚類特徵,如那小小的背鰭、略顯隱蔽的胸鰭和能够週期性開合的鰓,但它的魚鱗卻早已退化,取而代之的是一圈圈堅實的鱗片,為它提供了很好的防禦。 而在缺乏尾鰭的情况下,它卻擁有一條獨特的尾巴,這條尾巴不僅能像猴子般纏住海草、珊瑚等固定物,防止海流的衝擊,還因其方形截面而在動物界罕見。 美國克萊姆森大學機械系的研究團隊曾專門研究過海馬尾巴的抓握力,認為它的結構可以為工業機器人設計提供靈感。
海馬的眼睛也頗具匠心——兩隻眼睛可獨立轉動,類似變色龍的功能,使得它在獵捕獵物時擁有更為廣闊的視野。 而它的嘴部則演化成一個吸管狀的構造,在捕食時只需一瞬間便能將水和食物一同吸入口中,儘管這也限制了它只能吞下體積較小的獵物。 說到獵物,就不得不提海馬最愛的餐點——橈族類動物,尤其是一種形態酷似船槳的浮游生物。 這些微小的生物大約只有一毫米左右,即便它們具備極為迅速的逃逸反應(每秒可達500倍於身體長度的速度),海馬憑藉其悄無聲息的接近和迅捷的出擊,依然可以達到高達90%的捕獵成功率,這一數位遠遠超過了頂級獵手大白鯊僅55%的成功率。 海馬的狩獵秘訣便在於“慢中求快”:它們緩慢而無聲地靠近獵物,待獵物毫無防備之際,突然利用吸管嘴一舉將其吸入。
除了獵食獨特,海馬的消化系統也與眾不同。 它沒有胃,無法儲存食物,囙此必須不停進食。 通常,一隻海馬會每天攝入三千多次微小的食物,但在食物短缺時,它們憑藉低能量消耗能力,也能較好地熬過難關。
而在繁殖方面,海馬更是展現了獨到之處。 進入交配季節後,海馬會先通過一段優雅的“球舞”儀式來建立情感聯系,這種直立的舞姿頗具韻味,令人聯想到人類的浪漫。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實那腹部隆起、看似懷孕的其實是雄性海馬。 雄海馬擁有一個育兒袋,張開口表示已經做好接受卵子準備,隨後雌性將卵子傳遞進育兒袋,兩者面對面貼在一起完成受精過程。 之後,雄性不僅負責讓卵子受精,還為受精卵提供氧氣、補充營養、排出代謝廢物,並提供必要的免疫保護。 科學家甚至在雄海馬的育兒過程中發現了類似哺乳動物催乳素的激素。 幾周後,雄海馬會出現類似於孕婦臨產陣痛的抽搐現象,伴隨著宮縮將成百上千只幼小的海馬噴射而出。 由於幼體在體內發育時已經呈現完全體狀態,介於卵生與胎生之間,囙此其存活率雖只有千分之一到百分之一,卻依然高於那些產卵後就拋弃後代的魚類。 正是因為雄性承擔了繁殖大部分重任,海馬最終形成了一夫一妻的配對模式。 經過一次交配迴圈後,雌性可以在等待雄性繼續承載受精卵的同時,補充自身能量,為下一次排卵做準備,從而使得整個繁殖過程既節省能量又高效運轉。
此外,海馬還是唯一在海洋中能實現直立行走的魚類。 儘管有些魚類如帶魚、黃帶魚在水中也呈現似直立狀態,但它們的遊動管道還是沿著身體軸線,而海馬則完全垂直於身體軸線前行,完美演繹了直立行走的精髓。 科學家們一直在探索,這究竟是如何從普通魚類進化而來的。 2009年,澳大利亞的科研團隊發表論文指出,他們在淺海澳大利亞海域發現了一種與海馬十分相似的水准游泳“海龍”。 通過對比基因,他們確定海馬和海龍在大約兩千五百萬年前分道揚鑣。 可以推測,當時的海洋因地殼運動形成了大片淺水區,海草廣布、水流強勁,大魚類遊動顯得尤為吃力,正是這種環境促使海馬進化出依靠尾巴纏住海草和珊瑚的定居策略,而直立的身體姿態也囙此能更好地偽裝和伏擊獵物。 尤其是豆丁海馬,這一物種憑藉近乎章魚般的變色能力,在環境中遊刃有餘。 科學家在研究中發現,豆丁海馬會根據所寄居的珊瑚——通常為具有橙色或紫色兩種典型顏色的海鱔——調整自身顏色,其皮膚中存在的色素細胞正是這一能力的關鍵所在。
自古中外,海馬便被賦予了神秘的醫藥傳說。 《本草綱目》中記載,孕婦在臨產前食用海馬粉末並配合幹海馬,能够有助於順產。 日本也有類似風俗,認為孕婦隨身攜帶一隻幹海馬有助於保胎。 或許這源自海馬那直立的姿態與圓滾滾的腹部在形態上與孕婦頗為相似,更多的是寓意一種美好的象徵。 如果海馬真具備醫療功效,科學家勢必要深入研究其有效成分,並開發出替代品,因為野生海馬資源難以持續捕撈。 每年約有兩千萬只海馬被曬乾加工成補藥,而僅符合入藥標準的往往只是幾種顏色較淺的大型個體,這使得它們在野外的生存面臨巨大壓力。 中國與日本現時正致力於海馬養殖,希望能為野生種群分擔壓力。 與此同時,每年約有一百萬只海馬被用於水族觀賞貿易,但野生捕捉的海馬通常難以適應水族箱環境,反而是人工繁殖出的品種更為健康、飼養成本更低。
最終,對於水族愛好者來說,選擇人工繁殖的海馬遠比野生的更為明智。 最令人憂慮的,還是人類對海馬棲息地的破壞:海馬主要棲息在海草床、珊瑚礁和紅樹林中,這些生態系統普遍面臨環境污染和棲息地喪失的威脅。 當你發現海馬尾上纏繞的不是海草或珊瑚,而是棉簽、塑胶袋等垃圾時,意味著它們的生存正處於極度惡劣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