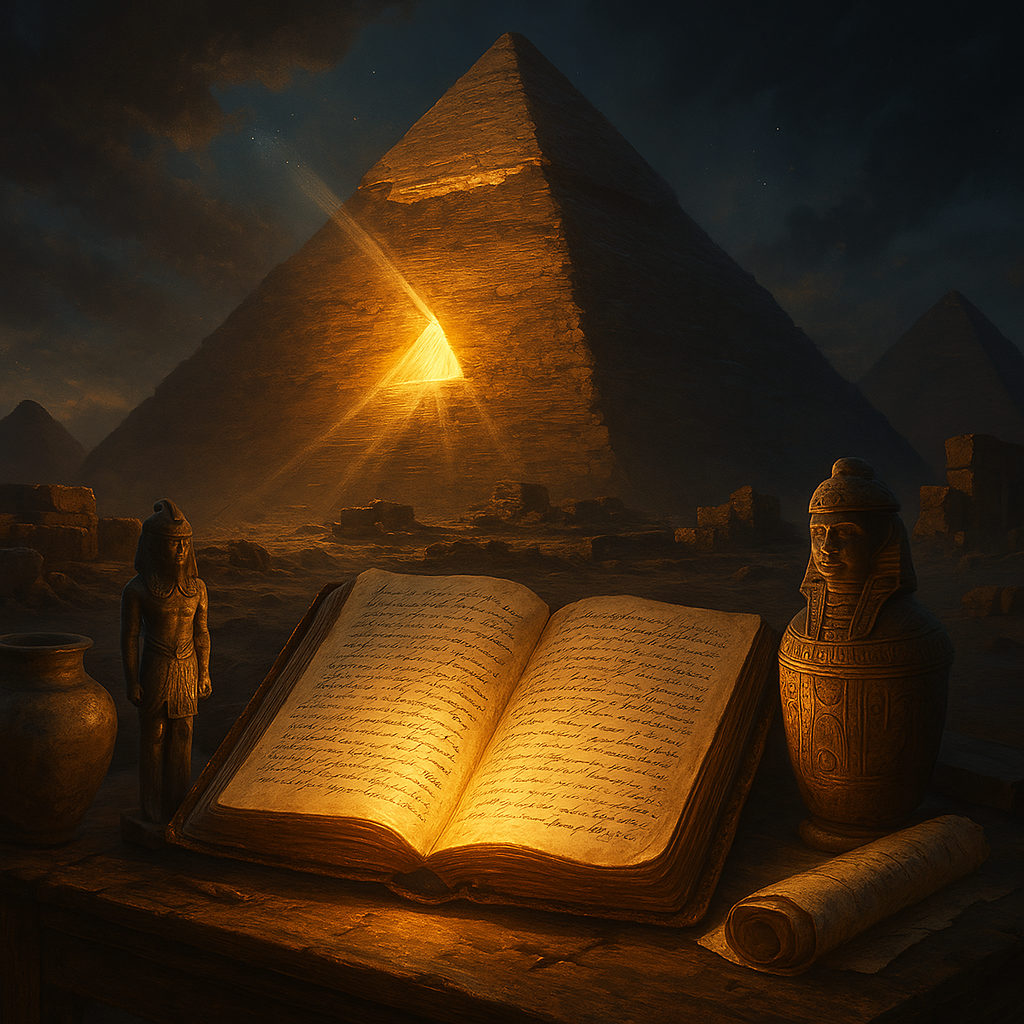酒精對生命體的影響遠超出你的想像! 人類飲酒竟似乎是基因早已註定的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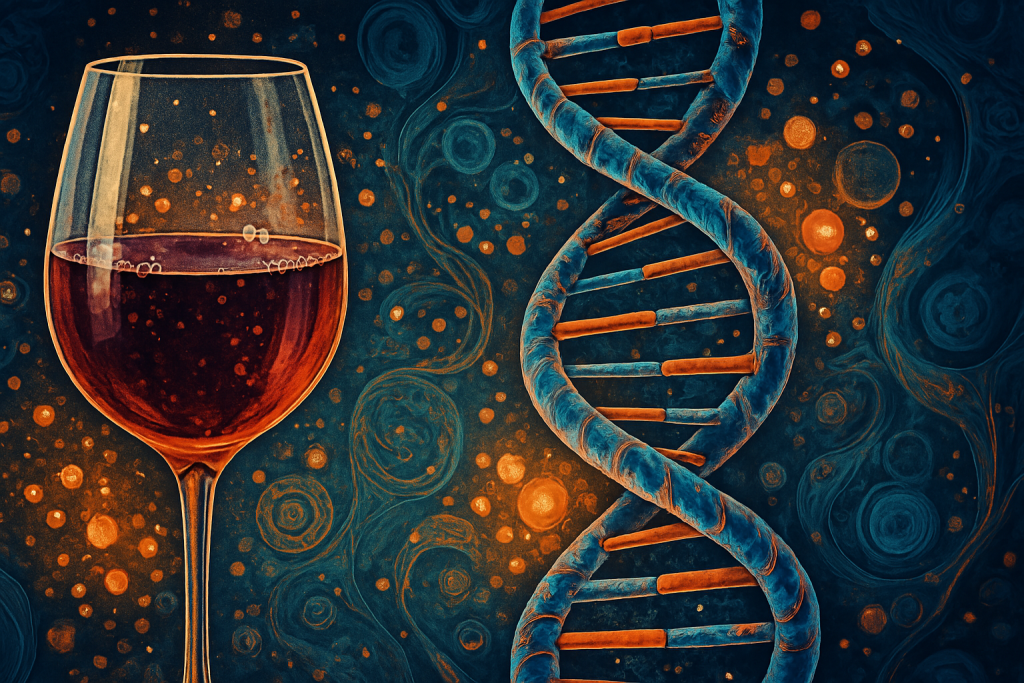
說到酒,不如今天就來探討關於酒的種種現象。 首先需要說明,根據權威醫學專家的研究,只要飲酒,就會對健康造成損害。 無論是小酌怡情、舒筋活血,還是所謂的適度飲酒有益健康,這些老生常談的說法均缺乏科學依據。 大多數醫學專家建議,滴酒不沾才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 聲明完畢,接下來讓我們正式進入今天的討論。
在南非有一種甜酒,也許你聽說過——阿馬魯拉酒。 該酒包裝極具特色,其瓶身印有一頭辨識度極高的大象。 那麼,為什麼選擇大象作為標識呢? 這就要追溯到這種酒的原料。 阿馬魯拉酒採用的是馬魯拉樹的果實,果實大小與雞蛋相仿,未成熟時呈綠色,成熟後則轉為黃色; 咬上一口,酸甜多汁,風味獨特。 馬魯拉樹主要生長於非洲南部的大草原,其果實深受狒狒、疣猪、鴕鳥以及大象等野生動物的喜愛,尤其是大象。 當果實完全熟透後,自然會發生發酵,轉變為含有酒精的飲品。
當地流傳這樣一個趣話:大象極愛這發酵的馬魯拉果。 只要大象走到一片開始落果的馬魯拉樹下,它便會停下脚步,把那裡的果實一掃而空。 大象在享用果實之餘,還將排泄物留在樹下,為樹木施肥,雙方關係密切,囙此當地人便稱馬魯拉樹為“大象樹”。 流言中還說,大象吃下馬魯拉果後會微醺、步履蹣跚,仿佛沉醉在幸福的酒意中。 然而,也有學者通過計算指出:成年非洲象體重至少在3000公斤左右,以人類平均75公斤的體重估算,相當於40個人喝下53度白酒會醉。 即便按照人均一兩酒量計算,大象也須飲下約2公斤、53度酒才能達到醉意; 而成熟的馬魯拉果釀成的酒,其酒精度最高也僅三度。 換言之,只有在短時間內消耗大約35公斤熟透的馬魯拉果,才可能讓大象醉倒。 單靠大象自然採摘果實,是不可能將自己灌醉的。 這一計算看似合理,但當基因學的證據擺在眼前,一切又顯得不盡相同。
既然說到基因,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不是只有人類與酒有著特殊的淵源呢? 猴子也愛喝酒。 傳說中,孫悟空大鬧蟠桃會時,不僅偷食蟠桃、當作仙丹充饑,還曾因倒飲禦酒而大發酒瘋,致使會場混亂。 這雖是神話,但現實中卻有類似的情形:在加勒比海聖基特島上,一群長尾猴竟專門偷遊客的雞尾酒來喝。 有人解釋說,島上盛產甘蔗,甘蔗成熟延誤採收後便會自然發酵。 猴子貪戀這種發酵甘蔗的滋味,以至於一旦缺乏,就紛紛覬覦遊客遺留的酒水。 觀察發現,與普通飲料相比,雞尾酒更能激發猴子們的飲酒興趣,喝得酩酊大醉後搖搖晃晃,仿佛一時沉醉於無限暢快中。
除了猴子,黑猩猩是否也會飲酒呢? 2015年,英國人類學家金伯利·霍金斯教授發表研究成果,其團隊在1995年至2012年間,不定期觀察了西非幾內亞柏蘇森林中的黑猩猩。 結果顯示,柏蘇森林中生長的一種“酒椰樹”——其枝葉可被用來釀酒,當地居民便裝置容器收集樹液,果不其然,黑猩猩成了“酒吧”常客。 研究觀察了26只黑猩猩,其中有13只表現出飲酒喜好。 據測算,黑猩猩一次可攝入純酒精高達84.9毫升,相當於人類喝下不到三兩半的53度白酒後便會醉倒。 儘管在體能上黑猩猩占優,但在酒量方面,人類仍展示出獨特優勢。
那麼,海豚會喝酒嗎? 我們都知道酒精易溶于水,海豚生存於海中,自然沒有酒水。 然而,1995年,海洋生物學家麗·斯坦納發現,海豚們的一種行為與飲酒後的狀態頗為相似,甚至顯得更為狂放。 它們喜歡“玩弄”河豚——這種魚雖劇毒,但若經過處理可成為美味佳餚。 大文豪蘇軾曾贊河豚為人間美味,並有詩雲“蔞蒿滿地蘆芽短”,足見其獨特魅力。 研究表明,海豚面對河豚時,常常小心翼翼地將其咬在嘴邊,嬉戲玩耍,而未敢破壞其表皮,以免中毒。 待全群“雨露均沾”之後,它們便一同遊離水面。 這種情景恰似它們在進行一種集體的“娛樂活動”,其行為狀態與飲酒後毫無疑問頗為相似。
綜合上述例子——南非大象、聖基特島猴子以及柏蘇森林的黑猩猩——似乎都顯示出酒精對動物行為的獨特吸引力,儘管明知過量飲酒可能導致行為失常、難以自控。 在野生環境中,任何因醉酒而導致的行為失範都意味著嚴重風險,但事實是,這些動物似乎總抵擋不住酒精的誘惑。 那麼,究竟為何在飲酒基因的較量中,人類反而顯示出先天優勢?
去年四月,人類基因學家瑪麗·賈尼亞克在《生物快報》上發表了一篇研究報告。 他在人體基因組中發現,人類具備一段名為ADH7的基因,該基因編碼的酶可迅速代謝乙醇。 賈尼亞克博士對85種哺乳動物的基因進行比對後發現,只有人類的ADH7功能强大。 以此來看,即便非洲象或亞洲象個頭龐大,其基因組中竟然沒有這種功能。 囙此,單純依靠體重來推算酒量是缺乏說服力的。 實際上,大象在飲酒方面確實顯得不堪一擊。 至於黑猩猩和猴子,賈尼亞克博士對比了它們的ADH7基因,同樣發現這兩者在代謝酒精上的能力遠不及人類。
為何唯有人類獨享這份特殊優勢呢? 博士從人類進化的角度提出解釋:約600萬年前,與黑猩猩分道揚鑣後,人類選擇了直立行走並轉移到地面生活,食物結構也囙此發生巨大變化。 樹上生活時,人類祖先主要食用新鮮的果實,但到了地面上,掉落的果實多已完全成熟,甚至開始發酵。 面對不斷攝入自然發酵的含酒精果實,只有那些ADH7基因突變後具有更强酒精代謝能力的個體,才能在野外生存中保持清醒。 久而久之,這種突變便在種群中穩定下來。 賈尼亞克博士還找到了其他證據,如馬拉加西的阿耶阿耶猴和食果類動物果脯,它們的基因測序結果同樣顯示出與人類極為相似的酒精代謝優勢。 至於大象,雖然它們也愛吃馬魯拉果,但畢竟攝入機會較少,主要飲食以草木為主,囙此難以練就“酒量”。
談到飲酒上癮,怎能不提詩仙李白? 李白好酒幾乎成了千古佳話。 據統計,他一生留下的詩篇多達一千七百餘首,其中近200首與酒有關。 杜甫在《飲中八仙歌》中提到:“李白鬥酒詩百篇”,意指李白只需鬥上一杯酒便能寫出百首詩。 嗜酒成性的他,甚至因酒而引起種種逸事。 今天我們不再詳述李白的逸聞,而是試圖從現代神經科學角度探討:為何有時飲酒後腦中靈感湧現?
哈佛大學心理系的一項研究利用腦成像科技探討人類思維時各腦區的活動情况,並聚焦於腹內側前額葉皮質與背外側前額葉皮質的功能分工。 簡單來說,前者與情感、幻想和虛構相關,而後者則主要負責推理、計算和判斷。 研究表明,這兩個區域在活動時存在此消彼長的關係。 當情感內側更為活躍時,理性分析就會受到抑制; 反之,理性活動占優則會抑制情感的流露。 正囙此,飲酒後腹內側前額葉皮質的活躍狀態更容易讓人情緒化,產生更多幻想和靈感。 這或許正是李白在酒後能妙筆生花的真正原因。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科學家們在嚴謹的理性思考中從未能靠飲酒來解方程。
總之,無論是人類還是其他動物,適時放飛自我、偶爾展露感性的一面,也未嘗不是一種生存策略。 正如鄭板橋所言,“難得糊塗”,有時過於理智反而會束縛住生活的豐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