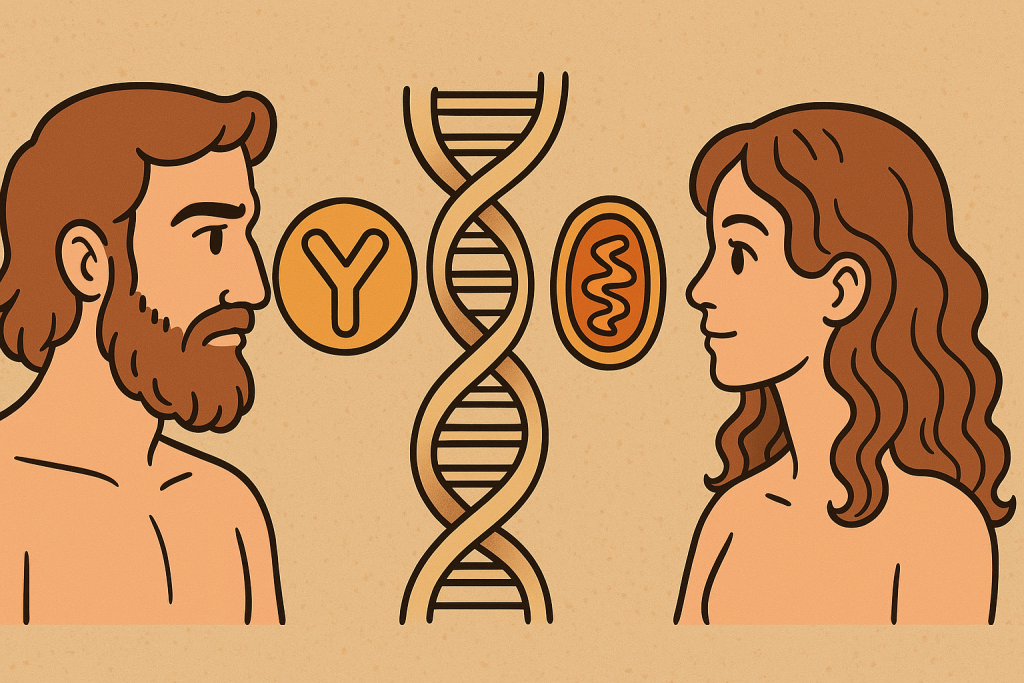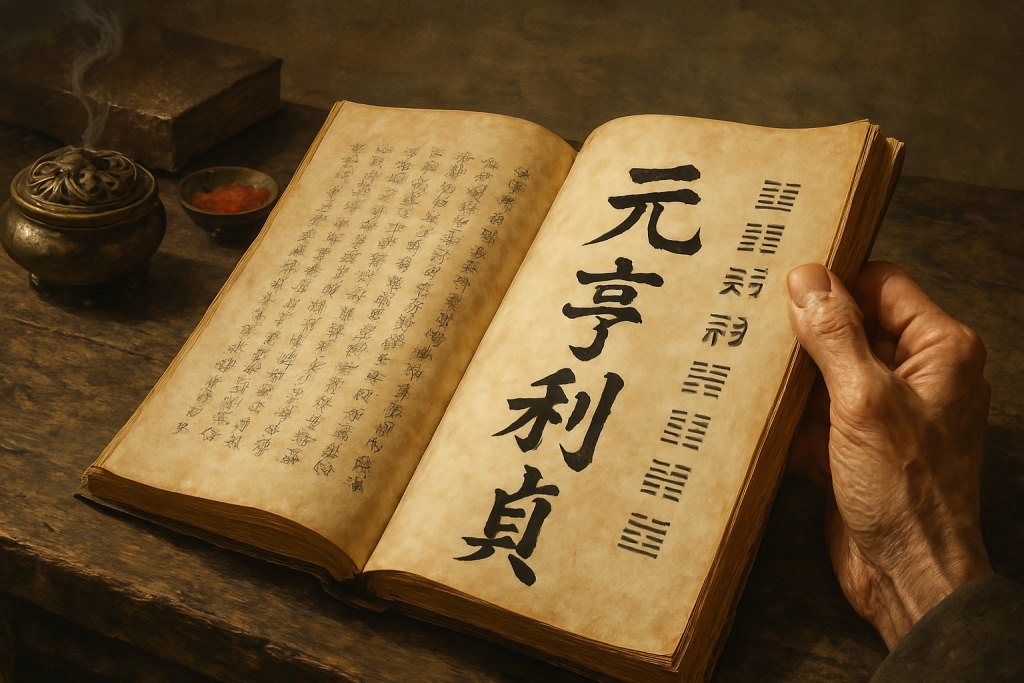最近咱們一直都在探討物種的起源,從簡單到複雜的生命演化過程。 但今天,咱們再把時間線拉得更久遠一些,一起來揭開生命從無到有的神秘面紗。 大家都知道,現時已知的生命一定是由有機物構成的,所以要想弄清生命起源的問題,就必須從這些有機物的誕生說起。 在地球剛剛形成時,並不存在任何有機物。 那麼,在當時極端的環境下,有沒有可能自然地產生生命所需的基本有機物呢?
針對這一問題,科學史上最經典的實驗——著名的米勒-尤裡實驗給出了探索方向。 1953年,芝加哥大學的科學家史丹利·米勒和哈羅德·尤裏成功在實驗室內重現了原始地球的海洋與大氣環境。 在一個密閉容器中,他們放入了水、甲烷、氨、氫氣和一氧化碳等物質,再以電極類比閃電,以熱源類比海底熱液噴口。 很多人或許以為有機物的形成會需要漫長的時間,但令人震驚的是,僅僅一周的時間,實驗中就產生了胺基酸、糖類、脂類等重要的生命基礎有機物。 雖然實驗並未直接合成DNA、RNA或蛋白質,但這至少證明了原始地球環境下產生生命基礎原料的可能性。
那麼,這個實驗是否完全揭開了生命起源的秘密? 顯然不是。 甚至連實驗的發起人米勒本人也坦言:生命起源的真相可能比任何人想像的都要複雜得多。 雖然米勒-尤裡實驗合成了基礎有機物,但卻沒有解釋胺基酸為何形成蛋白質,也沒有闡明DNA、RNA究竟如何誕生。 而且,更加尷尬的是,後續研究還質疑實驗的準確性——因為真實原始大氣可能並非如實驗設想的一般成分。 米勒教授本人也承認,他們的實驗設計存在猜測成分,並無直接證據。
另一個問題是實驗中產生的胺基酸分為左式和右式各占一半,但現實中生命僅使用左式胺基酸合成蛋白質。 那麼,地球上的生命為什麼偏愛左式胺基酸呢? 這一事實暗示地球上的胺基酸可能另有來路。
生命起源還涉及一個類似“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 在分子生物學領域,我們知道DNA、RNA和蛋白質之間相互依賴:DNA和RNA是遺傳物質,指導細胞生產蛋白質,但複製DNA、RNA又必須依賴蛋白質,似乎必須同時存在,顯然非常衝突。 為了解决這一難題,科學界提出了廣為接受的“RNA世界假說”,即認為RNA可能是最早實現自我複製、引發生命誕生的分子。 當然,這只是理論推測,尚無直接證據。
而NASA的研究則帶來了新的視角。 他們在一塊隕石中發現了大量左式胺基酸,這意味著地球上的生命起源或許與太空隕石墜落息息相關,這一發現使“泛精子假說”再次浮出水面。 該假說認為,生命可能最初誕生於星際空間,並借助彗星、小行星傳播到地球。 儘管現時缺乏直接證據,但已證實一些地球上的生物(如水熊蟲和苔蘚)確實能在太空極端環境下生存。
最近,科學界又提出了一個極具吸引力的理論——“PAH世界假說”。 科學家在星際空間中發現了大量的多環芳烴(PAH)和碳六十分子(巴基球)。 這些複雜的大分子早在太陽系誕生前就已出現,並且NASA通過類比星際空間的實驗表明,這些分子在超低溫下經紫外線照射,竟然會轉化為胺基酸和核苷酸——生命起源的基礎資料。 這意味著,星際空間可能天然孕育著生命的種子,並通過彗星、小行星播撒到各個星球。
但NASA的這一實驗仍留下一個懸念:這些生成的胺基酸究竟是左式還是右式? 若以左式為主,這個假說將顯得更加完美。
生命起源的探索遠未結束,我們可以從熵的角度進一步探討,但那將是另一個故事了,等以後聊熱力學第二定律時再一同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