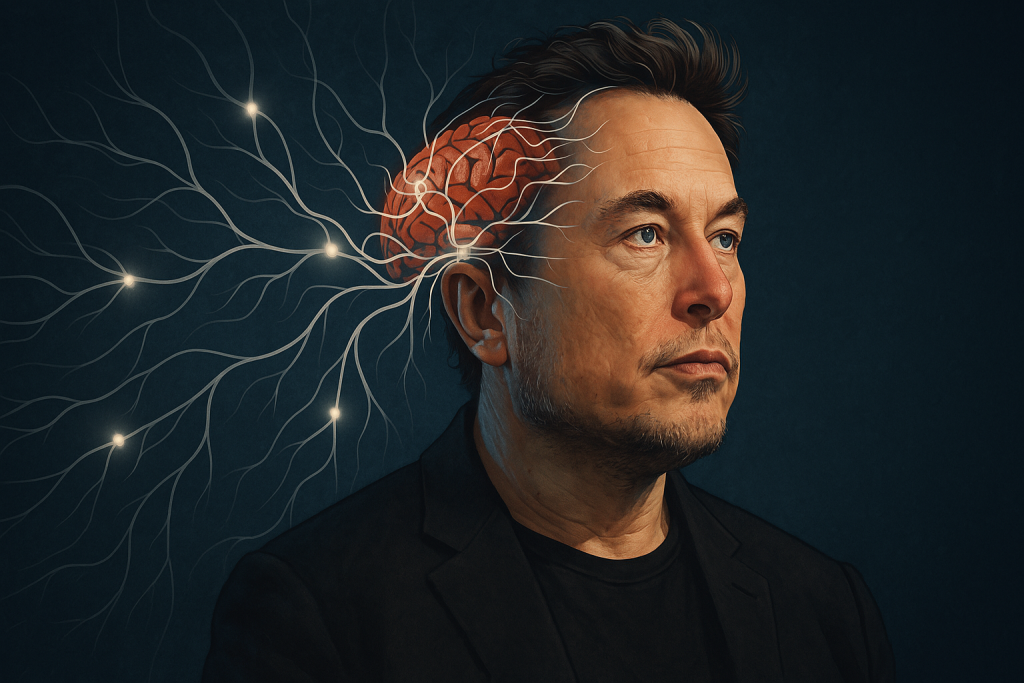二零一九年國際動物攝影師大賽年度冠軍,由中國攝影師鮑永清憑作品《生死時刻》榮獲。 照片中展示了一隻藏狐正捕獵喜馬拉雅旱塔(即土撥鼠); 藏狐驟然撲出,猶如奉上一枚“表情包”,而土撥鼠的動作恰到好處,整幅畫面極富張力。 其實,藏狐捕獵土撥鼠並非其常規手段,因為它的主要口糧其實是鼠兔。 既然上期非會員影片中探討了鼠兔,這期會員影片便聚焦於鼠兔生死對決中的宿敵——藏狐。

說到藏狐,其外形極具辨識度:頭大脖粗,既不似“紳士”亦非“伙夫”,反而流露出一種呆萌之態,完全不見狐狸一貫的狡黠靈動。 它最顯著的特徵便是一張大而方正的臉,眼睛、鼻子和耳朵均顯得十分小巧,整體造型頗為抽象,仿佛是一個對繪畫比例毫無概念的初學者的傑作。 儘管外表略顯粗獷,但天生含笑的表情總讓人感覺它正向你微笑,充滿親和力,這無疑也是其人氣頗高的原因之一。
在生物學分類中,藏狐隸屬於哺乳綱、食肉目、犬科的狐屬。 該屬共包含十二種狐狸,其中最知名的當屬赤狐。 赤狐憑藉強勢的生存能力佔據了環境較優地區,而其他狐類則多棲身於偏僻的冰天雪地或乾旱的沙漠草原。 我們的主角藏狐也未能例外,它們全部生活在海拔三至五千米、氣候嚴寒缺氧的青藏高原上。 生活在如此極端的環境下,藏狐面臨兩大生存挑戰:一是如何覓得充足食物,二是如何禦寒保暖。
首先談談保暖,藏狐主要依靠那一身濃密且修長的毛髮。 從頭至尾都覆蓋著長毛,使得它看起來略顯臃腫,臉部輪廓也因濃密的毛髮而更顯寬大,頗有幾分與赤狐相似之處。 藏狐的毛色主要分為三部分:後背呈棕黃色,側面則為鐵灰色,而腹部則是潔白色,尤其側面的鐵灰色更是其一大標誌。 其學名中包含拉丁詞彙“fairry lot”,似乎暗示著那大片鐵灰色的寓意。 雖然這身濃密長毛提供了優异的保溫效果,但在獵人眼中卻並非理想原料,因為毛質較硬粗糙、缺乏柔軟感,穿戴體驗不佳,僅能用於製作帽子,其經濟價值也囙此大打折扣,藏狐在這方面的運氣可謂不錯。
總體而言,由於飲食習性獨特,捕獵藏狐的獵人並不多。 說到食物,正如前文所述,鼠兔是藏狐極度依賴的主要獵物。 儘管作為捕食者,藏狐也會覓食其他動物,如冠軍照片中的土撥鼠,以及野兔、齧齒類、蜥蜴、鳥類甚至動物屍體等,只要機會出現,它們自然不會拒絕。 但歸根結底,這些僅充當“零食”般的補充,而鼠兔才是藏狐不可或缺的生存依靠。 事實上,有學者在青藏高原研究藏狐時,總是以鼠兔的踪迹作為尋找藏狐的名額,因為藏狐本身十分隱蔽。 如果某一區域鼠兔繁多,就有望觀測到藏狐; 若鼠兔踪迹罕見,則應及時更換場所,畢竟藏狐與鼠兔已是深度綁定的搭檔。 有人戲稱“兔死狐悲”,形容藏狐恰如其分。
細究藏狐的體態,不難發現其諸多特徵似乎都為捕捉鼠兔而生。 首先,其腿部相較於其他狐狸尤為短小,這顯然是為了適應草原上無遮蔽的環境,使其能够低伏身形,悄然接近獵物; 其次,從正面看那張標誌性的方臉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從側面觀察,藏狐的臉部線條修長,尤其是窄長的鼻子與嘴部。 這種設計使得當鼠兔鑽入洞中時,藏狐能够伸入洞內或挖掘洞口,從而順利捕捉到獵物,這無疑是一種專門針對鼠兔進化出的適應策略。
此外,正如前文所述,藏狐側面那片橫貫至尾巴的鐵灰色毛髮不僅在亂石堆中起到極佳的隱蔽效果,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與天空的灰色背景渾然一體,從鼠兔的視角看更是達到完美偽裝。 或許,這正是為了迎合鼠兔視角而進化出的特質。
有趣的是,在青藏高原上,藏狐幾乎以專門捕食鼠兔而聞名。 即便鄧羚或藏羚羊這類食草動物路過,面對藏狐時也幾乎毫無驚覺,而藏狐則始終只盯著鼠兔,專一程度可見一斑。 更妙的是,藏狐捕獵鼠兔時有時還會借助棕熊的力量。 棕熊同樣喜愛鼠兔,不過它不以快速追逐取勝,而是憑藉强大的體力將鼠兔挖出。 雖然藏狐本身也能挖掘,但若能借力於棕熊,無疑省力又高效。 囙此,每當看到棕熊正在挖掘鼠兔時,往往能在附近發現一隻藏狐靜候時機,一旦鼠兔驚慌逃出洞外,便迅速捕捉,聰明之舉盡顯無疑。 棕熊與藏狐這一組合不禁讓人聯想到北極熊與北極狐的合作:北極狐常常跟在北極熊身後,享用其捕食海豹後遺留下的食物,看來狐狸借助熊力混飯吃,似已成為一種古老傳統。
最後還有一件耐人尋味的事。 我們曾介紹過小丑蝦,提到其在獵物選擇和伴侶忠誠方面都表現出極高的專一性——只捕食海星,並實施一夫一妻制。 而巧合的是,藏狐同樣在這兩方面堪稱專一。 鼠兔是它們必不可少的獵物,而在伴侶選擇上,一旦攜手相伴,藏狐便會共同行獵、共同撫育幼崽。 因而,在大草原上你常能見到成雙成對的藏狐,它們幾乎沒有明顯的領地意識,即便多對共處同一草場也能和睦相處。 從這些行為不難看出,這些傢伙的天性早已寫在了它們那獨特的臉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