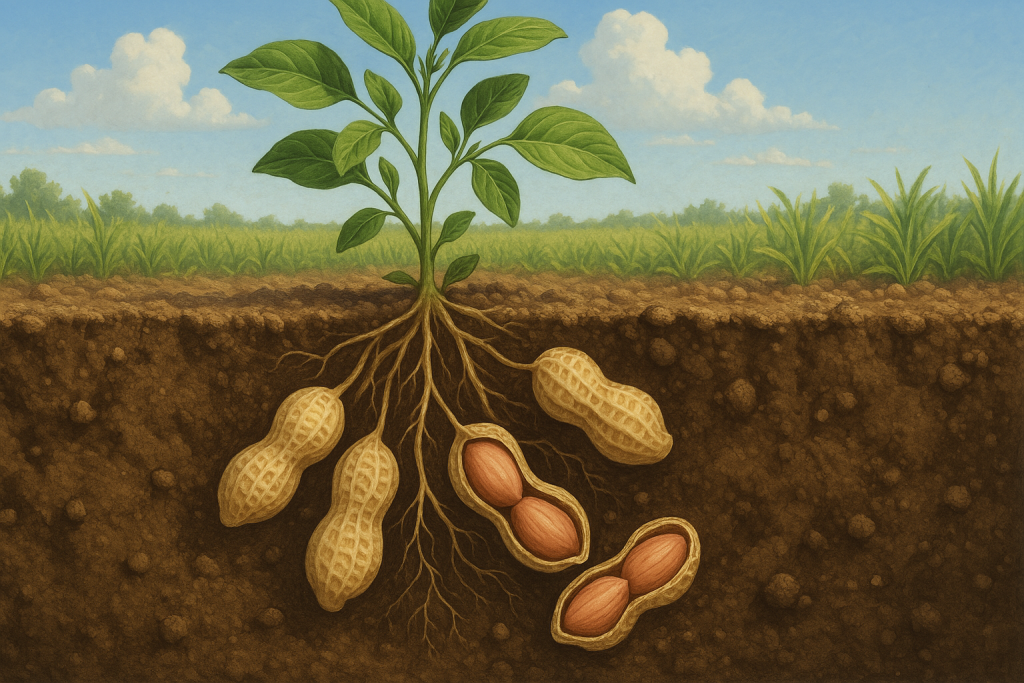大約五百萬年前,太平洋板塊與北美板塊分開,向西北方向挪動了一段距離。 臨走時還從北美大陸上“撕”走了一塊皮,硬生生扯出了一個狹長的缺口,也就是現在的加利福尼亞灣(科爾特斯海)。 這片海灣寬約160公里、長逾1000公里,形狀細長,十分特別。 而一般情况下,這樣被陸地包圍的小型海灣,多以淺海為主,水深一兩百米就算很深了。

然而,科爾特斯海因為是地殼張裂形成的,最深處居然超過3000米,非常驚人。 再加上那些通向岩漿層的裂縫還在不斷擴寬,產生大量的熱液噴口,將地層中的各種營養物質和礦物質源源不斷地釋放到水中,使其成為世界上“最有料”的海灣。 營養如此充足,自然吸引了無數海洋生物。 發明水肺潜水的法國人雅克·庫斯托(Jacques Cousteau)就曾稱科爾特斯海為“地球的水族館”,因為這裡的海洋生物實在是太豐富了。
比如,全球海洋哺乳動物一共120多種,其中約三分之一——包括虎鯨、藍鯨、座頭鯨、抹香鯨等——都能在此處出現。 再說海龜,共有多種類群,其中有5種也會來到這裡。 此外,還有包括各種鯊魚、蝠鱝在內的800多種魚類、上千種海鳥,以及數不勝數的無脊椎動物。 如果你想在一個地方盡可能看到更多的海洋生物,科爾特斯海絕對值得考慮。
然而,即便這裡擁有如此多原住的海洋動物,誰也沒想到,近幾十年裏居然闖入了一個可怕的“外來戶”,瞬間刷出了頂級存在感,甚至有成為這片海灣“新代言人”的勢頭。 當地漁民因為懼怕它,還給它取了個綽號“Diablo Rojo”,意思就是“紅魔鬼”。 它就是本文的主角——洪堡魷魚(又名美洲大赤魷)。
頭足綱的“十腕”成員
在之前提到章魚時,我們區分了頭足綱中的幾個主要成員。 頭足綱下有八腕總目,也就是章魚目,它們擁有八條觸手,辨識度很高。 還有十腕總目,也被統稱為烏賊類,顧名思義,它們有十根觸手。 烏賊類裏又可以再細分為墨魚和魷魚兩大類:觸手相對短、身上花花綠綠、游泳時像魚兒一般的,叫做墨魚; 觸手修長、身體像管子,遊動起來一竄一竄的,叫做魷魚。 這樣就能分清章魚、烏賊、墨魚、魷魚這幾個常見名詞的區別了。
提到魷魚,很多人腦子裏會直接浮現出鐵板魷魚、醬爆魷魚、炸魷魚圈等各種美食; 也有人會想到深海中那些神秘莫測的大王烏賊和大王酸漿魷——它們是世界上最大的無脊椎動物,也是抹香鯨的最愛,不過人類對它們的瞭解非常有限,很難直接拍到活體,可謂“神龍見首不見尾”。 正因如此,科學家常用同樣來自深海、體型也不算太小的洪堡魷魚來做研究對照。 洪堡魷魚最大可長到兩米,重約50公斤,和人類的體型差不多。
它最顯眼的武器,就是那十根觸手——其中八根較為普通,另外兩根特別長,佈滿大小不一的吸盤,而每個吸盤上都長著一圈鋒利的細齒,看上去就讓人不寒而慄。 一旦被它纏住,基本上就別想逃脫。 我們常在抹香鯨頭上看到的抓痕,其實也未必都出自大王烏賊,洪堡魷魚恐怕也貢獻了不少。 再加上它有和大王烏賊同款的堅硬鳥喙,戰鬥力不容小覷,叫它“小王烏賊”也不為過。
“紅魔鬼”的兇猛個性
洪堡魷魚之所以被稱為“紅魔鬼”,不僅因為它通體會變為紅色,更是因為它的性格十分兇猛。 白天,它們通常潜伏在深水區,夜晚則成群結隊地出來捕食,一邊瘋狂吞噬魚群,一邊身體還不斷閃爍紅色和白色——一會兒骨白色,一會兒血紅色,惡魔氣息十足。
更令人忌憚的是,它們會主動攻擊人類。 夜間下水的潛水夫要格外小心,因為洪堡魷魚會抓面罩、纏胳膊、搶攝像機鏡頭,逮著什麼就攻擊什麼,甚是囂張。 甚至有人看見它們攻擊體型較小的鯊魚。 也就是說,只要體型能“拿得下”,不管是不是天敵,都可能被它往嘴裡塞,可見其兇悍程度。 由此推斷,江湖上關於大王烏賊“反殺”抹香鯨的傳聞,也不算完全無法想像。
更甚者,為了填飽肚子,洪堡魷魚甚至會做出同類相食的行為。 喜歡釣魚的人都知道,路亞釣用的是模擬餌來騙大魚上鉤。 而釣洪堡魷魚甚至連模擬餌都不一定需要,一串帶倒刺的“假餌”就能讓它們沖上來。 釣起來不算難,但偶爾會發現,釣上來的魷魚竟然殘缺不全,明顯是被撕咬過,甚至有的只剩下可憐的一點軀體。 是誰下的手? 答案有些讓人後背發凉——正是它的同類。
科學家多次拍攝到洪堡魷魚同類相食的畫面:同群裏只要有年老的、弱小的、受傷的,就有可能成為同伴的目標; 若哪個倒楣蛋被釣線上拉離水面,或者被漁網纏住,就更容易遭到群體攻擊,仿佛在它們眼裡,“反正你也逃不掉,乾脆讓我先吃兩口”。 這種場面可謂相當“冷酷”。
那麼,它們同類相食到底有多普遍? 2010年,上海海洋大學海洋科學學院的劉必林博士發表了一項研究,分析了智利海域洪堡魷魚的生態。 研究人員共解剖了2000多只洪堡魷魚,結果發現超過一半的胃裡都有同類的鳥喙殘骸。 這意味著它們吃下去的不僅是魷魚的肌肉,連頭部都一起吞了。 對比其它獵物殘骸,同類相食竟然成為洪堡魷魚最主要的食物來源之一。 這讓研究者十分驚訝,卻也體現了洪堡魷魚極端的生存策略:弱者往往只是强者的囊中之物。
短暫壽命下的兇猛擴張
從人類視角來看,同類相食似乎難以理解,但對洪堡魷魚而言,這卻有其合理性。 大多數頭足綱動物都壽命短暫,比如體型最大的北太平洋巨型章魚,最大體重可超過70公斤,卻也只活三到五年; 一般的章魚更是僅有一兩年壽命。 洪堡魷魚也一樣,大多只有一兩年可活,卻要在這麼短的時間裏長到幾十公斤。 想想我們人類,嬰兒長到幾十公斤也需要好幾年,而洪堡魷魚卻僅用一年,還得獨自捕食,瘋狂進食才能快速生長。 在這種高强度的競爭壓力下,任何形式的“有機物”都不能浪費,同類自然也包括在內。
不過,如果它們能找到足够的正常獵物,同類相食的現象就會减少一些。 根據劉博士的研究,洪堡魷魚另一大食物來源是燈籠魚(即“晝夜垂直洄游”的魚類),這些小魚白天潜伏在深海,夜間才到上層活動,想以此躲避捕食者,卻還是被洪堡魷魚盯上了。 換言之,洪堡魷魚晝伏夜出的習慣,很可能就是因為要追捕燈籠魚而“被迫養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燈籠魚總量約占所有深海魚類的65%,可謂數量驚人,被洪堡魷魚列為“主要獵物”也就不足為奇了。
回聲定位與群體捕獵
一直以來,關於抹香鯨和大王烏賊相愛相殺的故事都有一個謎點:抹香鯨依靠回聲定位捕食,理論上說,越堅硬的物體反射越强,而軟體大王烏賊並沒有什麼硬骨頭,能反射的訊號並不多。 這個問題也同樣適用於洪堡魷魚——抹香鯨真的能通過回聲定位發現它們嗎?
美國斯坦福大學霍普金斯海洋站的威廉·吉利(William Gilly)教授是研究洪堡魷魚的專家。 他過去通常通過給魷魚裝上追跡標籤的管道,來觀察個體行為,但這只能掌握單只魷魚的動向,無法瞭解群體行動。 於是,在2007年至2011年間,他與俄勒岡州立大學的凱利·本諾伊特-伯德(Kelly Benoit-Bird)教授合作,嘗試用聲呐來追跡整群洪堡魷魚。 經過多次調整頻率和功率後,他們終於在聲呐圖上清晰地捕捉到了魷魚群以及單只魷魚的位置,這從聲學上證明,抹香鯨的回聲定位對洪堡魷魚確實是管用的。
更令人驚奇的是,吉利教授還發現,看似混亂的一群洪堡魷魚在獵殺魚群時,竟會步調一致地沿螺旋線向上移動,將魚群困在中間,如同形成一個“旋渦”,圍著目標一起進食。 等這一波捕食完成後,再回到魚群下方集合,繼續下一輪“旋渦殺”。 整個過程配合得天衣無縫。 這說明洪堡魷魚不僅能合作捕獵,而且似乎會通過身體閃爍紅白光來進行交流。 科學界一直猜測它們的變色或許是某種“訊號”,但直到看見這類群體圍捕現象,才更確定它們確實在“對話”,而且效率極高。 再加上洪堡魷魚擁有極大的眼睛,在昏暗水域也保持良好視力,用閃爍來溝通,可以說是完美的方案。
入侵科爾特斯海:幾十年大爆發
196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在著作《科爾特斯海日志》中,記錄了他和海洋生物學家愛德華·雷克茨(Edward Ricketts)於1940年在這片海域的航海冒險。 他們詳細描述了當時觀察到的各種生物,足足編錄了五百多種,可卻沒有提到洪堡魷魚。 這表明,至少在1940年時,科爾特斯海還沒有洪堡魷魚的身影。
然而僅過了三十多年,到上世紀70年代,科爾特斯海竟然爆發了洪堡魷魚大潮。 如今,估計數量已達兩千多萬,成了地球近幾十年“最成功的物種”之一。 那麼,這些從天而降的洪堡魷魚究竟來自哪裡? 從它們的名字就能看出來:它們的老家在南美洲的智利和秘魯海域,因為那兒有一股著名洋流——洪堡洋流。 原本,它們只喜歡較溫暖的熱帶海域,但不知為何,過去幾百萬年都沒“遠行”的洪堡魷魚,卻在最近幾十年開始了大規模擴散,一路向北蔓延,甚至在阿拉斯加海域都有了它們的踪迹,幾乎要席捲整個太平洋東岸,讓人匪夷所思。
科學家們對此展開了研究。 2017年,同樣來自上海海洋大學海洋科學學院的陳新軍教授發表了一項成果,指出洪堡魷魚的分佈與厄爾尼諾現象有密切關係。 每當厄爾尼諾導致海水變暖時,洪堡魷魚的分佈就會更為分散。 水溫整體升高,或許是它們繼續北上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這個解釋並不能完全說明它們為何會出現在水溫依舊較低的阿拉斯加。 更多研究認為,另一個關鍵因素是天敵的减少。
洪堡魷魚的天敵並不少,鯊魚、旗魚、金槍魚等肉食性魚類都會捕食它們。 但在某些海域,因為人類過度捕撈,這些大型捕食者變得越來越稀少。 以科爾特斯海為例,2005年因生物多樣性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但到2019年就進入了瀕危世界遺產名錄,破壞速度可見一斑。 當缺少那些“肉食狠角色”後,洪堡魷魚便有機會迅速繁衍。 它們每年就能性成熟,一年一代,再加上餌料充足,規模飛快壯大,在很多地方都紮下了根。 至於出現在阿拉斯加,更是表明它們開始“無視”寒冷水域的限制,確實可能要幹一番“大事業”。
會誕生新物種嗎?
說到這裡,很多人會好奇:物種一直在演化,那會不會有新的物種在我們眼皮子底下出現? 洪堡魷魚或許就能給我們提供一個例子。 假設原本生活在智利、秘魯等熱帶海域的洪堡魷魚,因為氣候或海洋環境改變,開始向北擴張,最終在阿拉斯加這種較冷的地方定居。 隨著時間推移,為了適應新的水溫和捕食環境,它們一定會發生各種變異,漸漸累積,出現與熱帶原住同類截然不同的特徵。 等到差异大到能形成“生殖隔離”時,一個新的魷魚物種便算誕生了。
洪堡魷魚的快速繁殖與世代更替,使它們具備了驚人的適應能力。 假以時日,若它們繼續往更多海域擴散,也不是沒有可能。 類似現象在地球生命史上數次上演——當一個物種擴散到全球,其所到之處的生態平衡往往會被打破。 就像陸地上的人類,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不過,要想真正佔領全球,並沒有那麼容易。 洪堡魷魚數量膨脹的地方,往往會吸引强大的捕食者回流。 比如,科爾特斯海的抹香鯨近年來似乎也在增多。 作為魷魚類的“一生之敵”,它們絕不會坐視洪堡魷魚大量橫行。 而且,洪堡魷魚口感鮮美,自然也會引來更多人類和海洋生物的捕獵。 想要“席捲全球”,或許並沒有它們想得那麼簡單。
總之,這些兇猛又聰明的“紅魔鬼”展現出了超强的生存與擴張能力。 雖然它們個體戰鬥力算不上海洋食物鏈最頂端,但通過群體合作和策略捕獵,就有機會對強敵構成威脅。 再加上頭足綱動物普遍擁有不俗的“智商”,它們在未來海洋中還能走多遠,確實令人拭目以待。 可要真正成為“海洋霸主”,它們要面對的挑戰,還多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