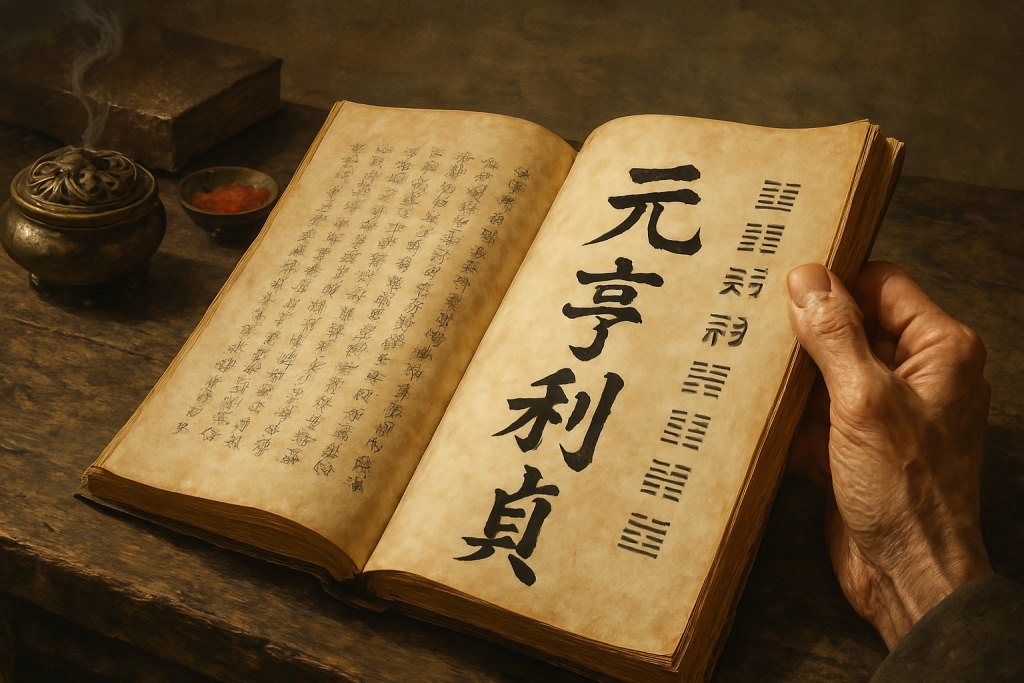南極最令人震撼的謎團,動物界最“純爺們”的代表! 帝企鹅究竟經歷了什麼?
讓我們聊聊帝企鹅的傳奇故事。 雖然都叫企鹅,但帝企鹅跟其他企鹅完全不是一回事兒。 它們的生存模式絕對可以用“匪夷所思”來形容,就算放眼所有鳥類,甚至地球上所有動物,帝企鹅都稱得上是一個奇迹。 看完這篇文章,你就會知道它們有多神奇了。

首先,有一件事兒大家容易產生誤解:我們通常說企鹅都在南極,所以可能會覺得是不是只有南極大陸才有企鹅? 是不是所有企鹅都生活在冰天雪地裏? 其實並不是這樣。 地球上現存的企鹅至少有十八種,只有兩種是地地道道的“南極居民”,一輩子只生活在南極洲:除了今天的主角——帝企鹅,還有阿德利企鹅。 其他企鹅的分佈非常廣,溫帶地區的澳大利亞、紐西蘭、南非、智利都有企鹅種群,甚至熱帶赤道的加拉帕戈斯群島也有企鹅。 所以其實絕大多數企鹅並不生活在南極大陸。 帝企鹅還有一點獨一無二:在所有企鹅之中,它是唯一一種終生都不用接觸裸露陸地的企鹅,要麼在海裡,要麼就在冰面上。 就算同樣生活在南極大陸的阿德利企鹅,繁殖的時候還要到陸地上找裸露地面築巢,但唯獨帝企鹅直接在冰面上繁殖——它們從出生到死亡,一輩子都不沾土,只生活在冰天雪地裏。 也就是說,世界上那麼多種企鹅,只有帝企鹅真正符合我們對企鹅的固有印象,是地地道道的冰雪代言人。
除此之外,帝企鹅生活在地球上最極端的環境裏,為了生存,它們演化出了動物界最不可思議的生存之道。 它們會在南極上空出現極光的時候,去做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兒,這是帝企鹅專屬的故事。
在生物學分類裏,帝企鹅屬於鳥綱企鹅目王企鹅屬。 這一屬裏有兩種企鹅,也是所有企鹅當中體型最大的兩種:王企鹅和帝企鹅。 跟帝企鹅相比,王企鹅的棲息地更靠北一些。 當年探險家從北面過來,先碰到王企鹅,一看這企鹅塊頭挺大,就覺得它們是企鹅裏的王者,所以給了它們“King Penguin(國王企鹅)”的名字。 後來探險家再深入南極大陸,又見到帝企鹅,結果發現它們比王企鹅還大,甚至能大到王企鹅的兩倍。 比國王還大的,只能稱“皇帝”了,於是帝企鹅(Emperor Penguin)的名字便誕生了。
那麼,帝企鹅到底有多大? 成年帝企鹅身高能超過一米,有些可達一米二,最胖時能長到四五十公斤,僅皮下脂肪就有三釐米厚。 在地球上所有鳥類當中,這重量能排在第五名,僅次於鴕鳥、鶴鴕、美洲鴕等那些“平胸類”的大高個。 帝企鹅屬於矮胖型,優勢在於比較敦實。 不過它們這四五十公斤的體重並不穩,一段時間後體重可能就掉到三十公斤左右。 到底怎麼回事,咱們稍後詳說。 總之,帝企鹅演化得如此龐大,大大縮小了它們表面積和體積的比值,理論上來說能减少散熱,更利於保暖,這也是它們演化成矮胖體型的原因。
除了身材厚實、皮下脂肪豐厚之外,帝企鹅還有其他抵禦嚴寒的妙招,最管用的就是它們那身羽毛。 帝企鹅的羽毛密度很高,據說每平方釐米就能長十一到十二根羽毛。 羽毛下麵還有羽絨,能形成空氣隔熱層,再加上羽毛能防水、羽絨能保暖,無論在水下還是在冰面上都能適應。 在冰面上時,它們唯一接觸冰面的部位是那兩隻腳,如何調節脚的溫度也是大學問。 溫度太高會浪費熱量,太低會凍壞細胞。 帝企鹅的血管擁有類似金槍魚、大白鯊的迷網結構,能够對四肢的血液進行熱交換,來精准控制脚部溫度。
有了這些對抗嚴寒的措施就足够了嗎? 還遠遠不夠! 尤其是當南極進入漫長的極夜,氣溫會下降到零下五十度甚至更低。 沒有羽絨服,光靠羽毛和皮下脂肪根本扛不住。 更“離譜”的是,帝企鹅不光要想辦法活下去,還偏偏挑在一年當中最冷的時候交配產卵、孵化小企鹅,想想都刺激。 那麼帝企鹅究竟是怎麼做到的? 這就是它們“高光時刻”所在。
對於世界上絕大多數企鹅來說,它們的繁殖策略和大部分動物一樣,選擇春暖花開的時候交配繁殖。 這樣生出來的小企鹅可以趕上夏天和秋天,食物充足,趁機多吃快長,在入冬前能基本長大,更容易活下來。 這一套看似合理,可是到了帝企鹅身上卻行不通,為什麼? 就因為它們體型實在太大。 如果在春天才交配,小帝企鹅到天冷之前根本來不及長到足够抵禦嚴寒的體格。 要想讓它們具備熬過第一個寒冬的生存能力,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小企鹅早點出生,也就是說交配產卵這一系列流程都得提前。
於是,就有了很“奇怪”的一幕:每年三月底、四月初,南極大陸開始降溫,準備進入冬季。 絕大多數在南極活動的動物都知道這裡的冬天多殘酷,紛紛往北遷徙,幾乎所有動物都離開這裡,只有帝企鹅“逆行”。 其實對帝企鹅來說,南極冬天最暖和的地方明明在海裡。 陸地氣溫零下四五十度乃至更低,海水卻最多零下二度而已。 帝企鹅若待在水裏會舒服很多,但為了繁衍後代,到了生育年齡的成年帝企鹅還是會毅然决然離開海水,爬上冰面,正面挑戰地球上最惡劣的環境。
帝企鹅的產卵地一般選在結了冰的海灣裏,越往海灣深處走冰層越穩固。 所以,它們上冰後,往往還要繼續走幾十上百公里。 對帝企鹅那小短腿來說,這段路並不輕鬆。 成千上萬只帝企鹅排著隊,搖搖晃晃地趕路,有時候還會趴下用肚皮滑行,像“名場面”一樣。 趕路幾天後,它們才能到達產卵地。 一到地方,公企鹅就迫不及待開始求偶。 帝企鹅是出了名的模範夫妻——一夫一妻制,但也只限一個繁殖季。 原因很簡單:去年的配偶不太可能剛好同時回來,往往會早幾天或晚幾天,沒人願意浪費時間,所以都會重新配對。 公企鹅用叫聲吸引母企鹅,如果雙方都有意向,會舉行儀式——倆企鹅面對面站著,彼此模仿對方動作:你低頭、我也低頭; 你抬頭、我也抬頭,像是拜堂,拜完就算“官宣”了。
接下來公企鹅面臨的大挑戰是爬到母企鹅背上——小短腿啊,平衡難找,尾巴一碰就算完事兒,目的達成就行。 到了大約六月初,母企鹅會產下一顆蛋,長約十二釐米、粗約八釐米,重量相當於八個雞蛋,外形像個頭稍尖的梨。 為了製造這顆蛋,母企鹅能消耗掉三分之一的體重,加上兩個月沒進食,必須立刻回海裏補充能量。 所以,她需要把蛋交給公企鹅。 別看這事兒好像有手就行,但問題是它們沒有手! 母企鹅只能把蛋放在冰面上,後退兩步,讓公企鹅去“撿”,如果不小心蛋滾遠了,公企鹅在一分鐘之內沒接好,蛋就可能會凍死,殘酷至極。 所以它們往往要花時間默契配合,等交接穩妥後,母企鹅就趕緊動身回海裏。 接下來的孵蛋任務,全靠公企鹅獨立完成。
這種模式和之前提到的海馬有些相似:雌性耗能量產卵,雄性耗能量孵化,公平又合理。 只不過帝企鹅的雄企鹅孵蛋過程堪稱最“爺們”的。 當母企鹅離開後,公企鹅就正式進入漫長的孵蛋期。 接下來的六十五天裏,無論它走到哪兒,蛋都得隨身帶著。 它會把蛋放在兩腿中間、肚子下麵那塊血管密集、溫暖的“育兒袋”裏,這裡還能讓企鹅蛋相對穩妥。 剛才也說過,蛋絕對不能掉出育兒袋,否則在零下五十度的環境裏,一分鐘內就會凍死。 公企鹅自己也明白這一點,非常謹慎。 科學家甚至發現,它們在母企鹅產蛋之前,就會提前抱個雪球練習如何孵蛋,仿佛在演練,以防真蛋孵化時失手,心思之縝密,令人佩服。
公企鹅的厲害之處還不止於此。 基本上母企鹅離開時,南極就已經進入極夜,產卵地附近會連續兩個月見不到太陽,而這段時間正好是公企鹅孵蛋階段,也是南極一年裏天氣最惡劣的時期。 氣溫常常能降到零下五十多度,還會伴隨狂風暴雪,最强風暴風力甚至超過十二級,宛如人間地獄。 可憐的公企鹅不僅要抗凍,還得保護懷裡的企鹅蛋。 為了熬過寒冬,它們唯一的辦法就是“抱團取暖”。 這可能是動物界最壯觀的場景之一:在炫麗極光的映襯下,幾千只帝企鹅圍成一個大圓陣,背對狂風、緊挨在一起,縮脖埋頭。 擁擠到什麼程度? 每平方米能站十到十二只企鹅,幾乎沒有活動空間。 如此一來,企鹅群中心溫度能達到零上三十多度,比外界高出七八十度,非常誇張。
那最外圈的企鹅豈不是被凍慘了? 帝企鹅的智慧就在這兒:科學家通過長時間拍攝發現,它們會不斷調整位置。 大約每三十到六十秒,某只企鹅挪一步,連帶引發連鎖反應,像波浪一樣擴散,所有企鹅都會動一下。 這樣幾小時後,最裏圈和最外圈的企鹅就能輪換一遍。 風力大的時候,上風口的企鹅扛不住了,就換到下風口,其他企鹅再頂上去。 如此迴圈,整群企鹅才能一致對外,所有成員都有避風取暖的機會。 正是憑藉如此巧妙的團隊合作,這群“純爺們”撐過了極夜裏的兩個月。 到了八月初,太陽再次升起,企鹅蛋也紛紛開始孵化,更重要的是,出海打魚的母企鹅們終於要回來了。
這時的小企鹅陸續破殼,公企鹅看著出生的小企鹅會非常興奮,沒事就抱著它們“閒逛”,像人類“曬娃”一樣炫耀。 按照“正常劇本”,蛋孵化時母企鹅應該恰好趕回。 她們在海裡這兩個月拼命進食,不僅補足自己消耗的能量,還帶回儲存的食物反芻給小企鹅吃。 母企鹅回歸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幾千只“老爺們”中找到自己那位老搭檔。 只能靠叫聲相互辨認,所以這個季節的企鹅群會突然熱鬧起來——母企鹅在外頭叫,公企鹅在裡面回應。 奇妙的是,光憑叫聲它們就能精准地找到彼此。 接著便要進行二次“交接”:如果蛋沒孵化完,就把蛋移交母企鹅; 如果小企鹅已經孵出,就把它交給母企鹅。 母企鹅肚裡有食物,能第一時間反芻喂給小企鹅; 而公企鹅這邊從三四月上岸後足足有四個多月沒吃東西,體重能掉二十公斤,必須趕緊回到海裡進食,同時捎帶給小企鹅弄點口糧回來。 接下來,夫妻倆會輪流出海、輪流餵食。 等小企鹅滿六周左右,就能離開育兒袋,自己凑在一起,就像進了“幼儿園”,父母雙方能同時出海,帶回更多食物。 每次回到冰面,它們就去“幼儿園”找自家娃喂飯,然後再送回去,如此往復,直到小企鹅漸漸長大。
然而,小企鹅平安長大並不容易。 比如,小企鹅已經破殼了,但母企鹅遲遲不回怎麼辦? 這時候,“純爺們”又會有驚人之舉:雖然已經四個月沒進食,但公企鹅還是會從胃裡吐出類似乳汁的液體,讓小企鹅至少暫時不會餓死。 這只能算應急之策,若母企鹅十來天還不回來,公企鹅就撐不下去了,小企鹅最後只能餓死。 除此之外,猛烈風暴也會沖散“幼儿園”,吹散的小企鹅要麼被凍死,要麼走失,父母也再找不到它。 到了春天,還有猛禽回到南極,比如巨鸌、賊鷗等,它們也會攻擊小企鹅。 種種天災人禍導致小企鹅的死亡率很高,大約只有五分之一能熬過第一年,十分殘酷。
那些倖存下來的小企鹅到了一月左右會褪去灰色絨羽,換上能游泳的羽毛,變成成年帝企鹅的樣子。 隨著海冰融化,它們就能下水自力更生了。 再過四五年,它們也會像父母那樣,在一年最冷的時候登上冰面,去做“地球上最了不起的事兒”。
帝企鹅一進海裡,行動比在陸地上靈活多了。 它們有專門的肌肉來控制羽毛角度,下水時,會把保溫用的空氣層擠出一部分,所以你總能看到下水的帝企鹅身後帶著一串氣泡。 原本臃腫的體型變得流線型,速度更快。 除了游泳之外,帝企鹅還是潜水高手:它們的血紅蛋白結構適應低氧環境,還能主動關閉一些器官,降低新陳代謝。 而更重要的是,它們的骨頭和一般鳥類完全不同:一般鳥類骨頭是空心的,為了减重好飛行,但帝企鹅的骨頭卻特別緻密,能承受五十個大氣壓,所以可以下潜到五百多米深的海底,潜水時間可超過二十分鐘,非常厲害。
那麼,帝企鹅吃什麼? 正常情况下,它們在五十米以內的淺層水域捕食,或者貼著冰面吃些南極“飛魚”、磷蝦,也會下潜到更深的海域去捕魷魚。 這些都是常規口糧。 但在海裡,帝企鹅也面臨最危險的捕食者。 之前提到的豹海豹和虎鯨就是它們的主要天敵,尤其豹海豹捕企鹅以兇殘著稱,經常把它們在水面上來回摔打,撕碎後吞下,看得讓人頭皮發麻。 只是,食物鏈上的捕食關係並不算帝企鹅真正的危機,它們現時面臨的最大威脅還是氣候變暖。
之前我們在談北極熊的時候提過,北極熊捕食海豹非常依賴海冰; 海冰面積不够大、維持時間不够長,北極熊就會挨餓。 帝企鹅同樣如此,它們的產卵地需要穩定的海冰支撐。 如果海冰過早融化,小企鹅還沒來得及換羽毛學會游泳,就會被淹死。 比如2019年曾有一項研究指出,帝企鹅的第二大產卵地——哈雷灣,連續三年遇到極端天氣和海冰不足,每年都有數千只小企鹅不幸死亡。 科學家按照現時的變暖趨勢推測,到2100年,帝企鹅數量可能會下降80%,從如今的“近危”變成“極度瀕危”,形勢相當嚴峻。
對帝企鹅來說,這事兒真是兩難。 尤其是孵蛋的公企鹅們在零下五十多度寒風中,他們肯定希望能暖和一點; 可氣候一旦變暖,它們的後代又可能難以存活,實在衝突。 或許只能用一句話來形容它們對氣候變暖的態度——“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歎劍,怨天寒”,讓人心生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