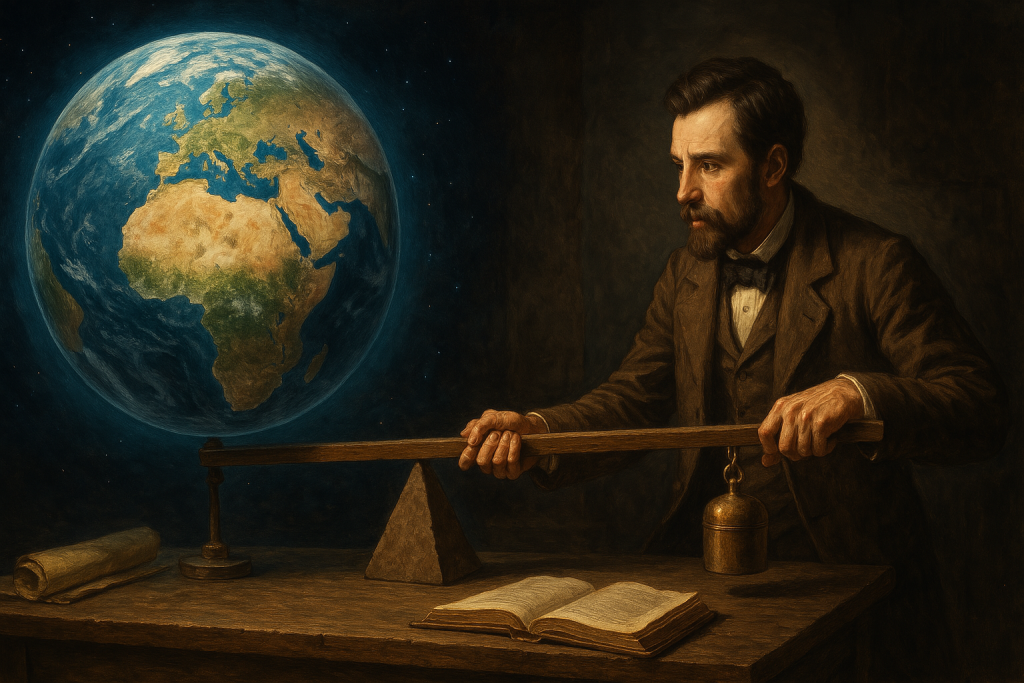本期節目從2009年7月28日哈爾濱極地館的一次驚心動魄的救援說起。 那天,在深達6米的北極水族箱裏,極地館正舉辦一場自由潜水比賽——選手需在無呼吸裝備的情况下潜入冰冷水底,拼時間,爭取成為館內的馴養員。 26歲的楊雲順利入圍決賽,卻在上升至極限時突感腿部劇烈抽筋,無法自控地急速浮起,生命危急。

當場的潛水夫和工作人員尚未察覺異狀,一道巨大的白色身影便破水而出——正是白鯨米拉(Mira)。 它輕輕用嘴咬住楊雲的小腿,將他緩緩頂至水面。 待楊雲恢復呼吸,並向岸上同行說明原因後,才知因抽筋陷入險境。 幸得米拉及時發現並施以援手,才讓這位選手逃過一劫。
米拉的英勇事蹟很快被各大媒體報導。 然而,提到“最出名”的白鯨家族,這個北極精靈還有更多令人難以置信的傳奇。
圓潤額頭與“可動脖子”
看過抹香鯨的朋友可能記得它那碩大的“額頭”,就像南極絨企鹅一般圓潤。 而白鯨的大額頭更勝一籌,表情自然微笑,活脫脫一個海底的絨企鹅——唯一不同的是,它們生活在北極。
就如抹香鯨一樣,白鯨額頭內同樣充滿了富有彈性的“鯨油”,助它聚焦聲波,發出或接收回聲定位訊號。 阿拉斯加大學的羅斯托德教授曾形象地將它比作“裝滿溫暖油脂的氣球”。
還記得它那宛如陸生哺乳動物的自由轉頭嗎? 大多數鯨類的頸椎骨是融合在一起的,導致游泳時脖頸僵硬,轉身必連帶身體一起轉。 而白鯨的七塊頸椎並未融合,使它能靈活地左右張望,脖頸處還留有褶皺,宛如水下動物界的“肩膀”,遊姿靈動無限。
消失的背鰭與進化之巧合
仔細觀察你會發現,白鯨沒有背鰭——這是它們適應北極冰層環境的結果。 常年在冰縫和冰下穿行,背鰭極易被冰層刮傷; 沒有背鰭,遊動時便不會被卡住、撞裂。
同樣生活於北極的弓頭鯨也失去了背鰭,儘管它們一個是齒鯨一個是須鯨,進化路線完全不同,卻都退化出相同特徵,這便是自然選擇下的趨同進化。
北極熊與“囚困”
白鯨可長達4~5米、重達1~2噸,而北極熊體重不過半噸,雖能短暫潜水,卻難以捕捉它們。 但當白鯨被虎鯨驅趕到冰層密佈的海域,偶爾會在冰洞處交換呼吸空氣,一旦錯過回聲定位最佳的洞口,它們就可能被困在冰面下,無法一口氣遊回開闊水域。 此時,北極熊可借機跳入冰洞捕食。
難道白鯨就此無路可逃? 並非如此——要麼待虎鯨離去,再返回熟悉水域; 要麼仰仗“弓頭鯨大哥”——它們那堅硬的頭骨能破開薄冰,打出新的呼吸孔; 要麼自己頂撞薄冰,哪怕額頭再柔軟,也能鑿出一條生路。 白鯨們常與弓頭鯨相伴,彼此互助,共度生死。
與人類互動的天賦
說到白鯨最與眾不同的地方,還是它們熱衷於與人類互動——在世界各地的海洋館裏,白鯨是為數不多能被馴養、並願主動交流的鯨類。
1984年,被譽為“海洋哺乳動物醫學之父”的山姆·李奇維博士在海洋哺乳動物基金會的水箱中,意外聽到一頭名為NOC的白鯨發出“OUT!OUT!OUT!”的聲音。 岸上的同事根本沒人喊它,經過確認,聲音正是NOC模仿人類發出的。 此後,李奇維博士對NOC進行了專門訓練,並在2012年發表論文指出,白鯨要想發出人類聲調,必須有意識地改變自身發聲機制,難度極高。 NOC在青春期的四年間堅持嘗試,後來性成熟後便不再模仿,也許它已自證:與人類語言的橋樑難以長存。
事實上,模仿人類並非NOC的孤例。
- 1950年,生物學家威廉·舍維爾與芭芭拉·勞倫斯在野外錄下的白鯨叫聲,就被形容為“一群孩子在遠處吵鬧”。
-溫哥華水族館中,一頭15歲的白鯨Lagossy能分辨並“喊出”自己的名字。
-日本海洋世界的白鯨Neke,也曾清晰地發出“哦哈妖”這樣的音節。
不止模仿人聲,白鯨還會模仿其他海洋生物:虎鯨、海豚的回聲定位音,甚至座頭鯨的歌聲。** 2020年**,克裡米亞科克特海洋世界的一頭4歲白鯨,轉場至海豚館僅兩個月,就開始發出海豚般的叫聲。 因其語言學習能力,於是有了“海洋裏的金絲雀”這個綽號。
“間諜鯨”赫瓦基米爾的網紅之路
說到最紅的網紅白鯨,非2019年4月出現在挪威哈默菲斯特鎮海灣的那位莫屬。 漁民們驚見一頭上身綁著相機支架的白鯨,背帶上甚至印著“聖彼德堡裝備,產自俄羅斯”的字樣。 一時謠言四起:它是軍方間諜鯨? 但俄羅斯方面很快澄清,若真為間諜,背帶上怎會留聯繫方式? 工作更可能僅出自民間科研組織,至今無人認領。
這位不速之客安頓下來後,當地居民為它舉辦了一場“真名大賽”——
1.“詹姆斯·貝魯加特工”(取自詹姆斯·邦德)
2.“焦爾”(發現它的漁民名字)
3.“赫瓦基米爾”(挪威語“赫瓦”意為“鯨”,“基米爾”呼應俄式名字)
最終,它得名赫瓦基米爾(Hvaldimir),迅速成為網紅。
- 2019年5月4日,25歲的遊客伊娜·曼西卡遊艇失手機落海,赫瓦基米爾竟將手機叼回水面,還定格了一段“人與鯨共舞”的溫馨畫面。
- 同年9月2日,49歲的約翰森拍到赫瓦戲耍海鷗:先偷襲、輕咬,然後又將魚還給對方,仿佛在捉弄它又不真傷害。
- 9月25日,皮划艇運動員阿西姆·拉森用頭戴運動相機錄製赫瓦,結果相機被它“偷襲”打落海底,隨後赫瓦又深潜拾回,分毫未損地歸還。
然而,人們對它的熱情有時也過了火。 赫瓦遊至阿爾塔港後,不少年輕人駕船圍觀,甚至有人粗暴地將拖把塞進它的嘴裡。 海洋生物學家伊夫觀察到,赫瓦的體重有所下降,背部還出現了螺旋槳劃傷。 它自阿爾塔離開後便再未被見過。 希望這位“網紅鯨”已安全歸隊,重回北冰洋的自由群體。
種群回暖的好消息
作為本期對白鯨的致敬,我們不想在悲傷中落幕。 自從全面禁止商業捕鯨以來,白鯨數量正在恢復。 到2017年,全球白鯨數量約為20萬頭,除阿拉斯加庫克灣亞種仍屬“極度瀕危”外,其餘21個種群均已恢復為“無危”級別。 願更多像米拉、NOC和赫瓦基米爾這樣的白鯨,在北極海域自由暢遊,繼續用它們的微笑和智慧,溫暖人類的心。